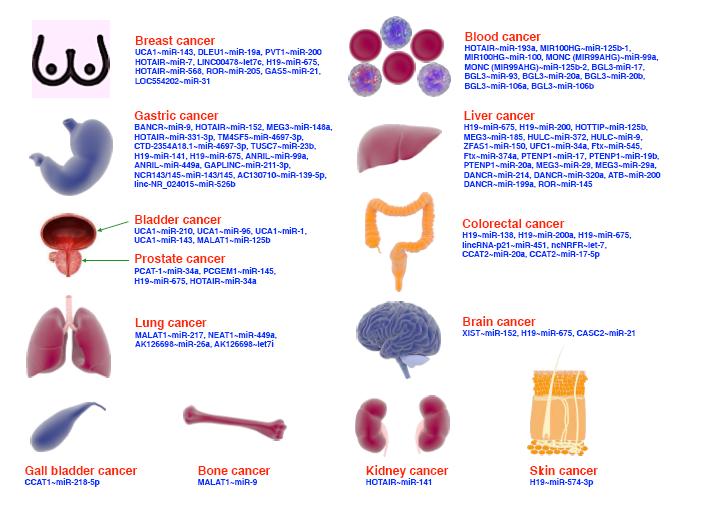糖尿病视网膜神经变性(DRN)是在高血糖环境中由于氧化应激、微血管损伤、代谢紊乱、神经营养因子失衡和免疫损伤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正常功能受损。神经元和神经胶质功能障碍的丧失参与血视网膜屏障破坏,血管反应和神经血管耦合受损,从而导致微血管病变和神经变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DRN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相关。更深入地了解神经血管损伤的发病机制可能会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提供新的和更有效的预防策略。
引用本文: 李虹蓉, 汪浩. 糖尿病视网膜神经变性的研究进展.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0, 36(6): 479-482.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190702-00208 复制
版权信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期刊社《中华眼底病杂志》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改编
糖尿病视网膜神经变性(DRN)是在高血糖环境中由于多因素共同作用,包括氧化应激、微血管损伤、代谢紊乱、神经营养因子失衡和免疫损伤等造成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NVU)的正常功能受损,尤其是周细胞的丢失;NVU的逐渐破坏最终表现为临床上可识别的视网膜病变的迹象。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实验模型的研究表明,周细胞脱落发生在内皮细胞丢失之前。周细胞的损失损害了毛细血管的完整性,并导致血视网膜屏障(BRB)和血管渗漏增强。因此,视网膜神经变性越来越被假设为与血管改变相关,并且与DR发病机制有关。目前对DR的管理主要集中在视网膜结构和视力已经受到影响的晚期阶段;而一旦视网膜病变临床可见,视网膜损害很难逆转且DR进展的风险增加。因此,更深入地了解神经血管损伤的发病机制可能会为DR提供新的和更有效的预防策略。现针对DRN的发病机制、临床检测方法及治疗意义作一综述。
1 发病机制
视网膜是由三级神经元通过突触构成神经视网膜和RPE细胞相互连接形成[1]。光直接刺激的神经元是光感受器细胞,主要包括视杆、视锥细胞;来自视杆、视锥细胞的神经信号经历视网膜的其他神经元处理,以RGC中动作电位的形式输出,其轴突形成视神经[2]。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视网膜从双重血液供应中获得氧气,双循环的存在使视网膜氧合作用比较特别[3]。光感受器和外丛状层的较大部分间接地从脉络膜毛细血管中获得营养,而内层视网膜由视网膜中央动脉分支形成的浅表和深毛细血管丛供应。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光刺激选择性地提高内部视网膜层中细胞的代谢需求,导致视网膜血管扩张,而呼吸100%氧气导致它们收缩[4]。视网膜中氧气供应和消耗之间的微妙失衡使视网膜处于缺血性损伤风险中,视网膜内层对缺氧刺激的敏感性最高[5]。现在大多认为视网膜缺血在DR中起主要作用。据报道,RGC对急性、短暂和轻度全身性低氧应激以及糖尿病中发生的神经退行性过程高度敏感[6]。细胞功能障碍与生化改变相结合,如高血糖假性缺氧、蛋白激酶C途径活化、氧化应激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的增加被认为会引发炎症级联,引起视网膜损伤[7]。
视网膜“神经血管单位”包括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基底膜和视网膜血管元件(内皮细胞、周细胞)之间错综复杂的功能耦合和相互依赖性[8]。对维持血视网膜内屏障(IBRB)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同时动态根据代谢需求调节血流量[9]。由紧密连接复合物组成的IBRB对于调节血管腔和神经视网膜之间的代谢物交换有重要作用,维持了神经元功能所需的适当环境。而在糖尿病高血糖环境中,多种因素影响视网膜的完整神经血管单元,导致神经炎症、神经胶质细胞增生或激活;视网膜神经变性在视网膜显著血管病变之前发生[10]。神经变性的标志是神经细胞凋亡和神经胶质功能障碍,而BRB破坏、血管退化和微血管血流动力学反应改变(神经血管耦合受损)是早期微血管异常的主要特征。在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环境中,先天性免疫系统的早期激活,补体系统和微小的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引起神经元谷氨酸能和多巴胺能神经递质信号传导的改变,降低突触蛋白表达,改变神经胶质功能[11-13]。谷氨酸的积累和神经保护因子的丧失引发VEGF的激活,这在BRB破坏中起关键作用。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的逐渐破坏最终表现为临床上可识别的视网膜病变的迹象,尤其是周细胞损失。有关DR模型的实验研究表明,周细胞脱落发生在内皮细胞丢失之前[14]。周细胞的损失损害了毛细血管的完整性,并导致BRB的逐渐破坏和血管通透性增加[15]。Müller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等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的反应性进一步增加。细胞黏附分子在视网膜脉管系统上的上调导致循环单核细胞的白细胞增多和浸润增加,损害视网膜组织的神经毒素和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增多。进而出现临床上可见的微动脉瘤、出血以及视网膜组织中脂质渗出物的渗漏和功能性毛细血管的丧失,导致视力损害。若不及时治疗,DR进展到增生期,包括新生血管形成、黄斑水肿、玻璃体积血和瘢痕组织形成,最终导致失明。神经元和神经胶质功能障碍的丧失参与BRB破坏,血管反应和神经血管耦合受损,从而导致微血管病变和神经变性。因此,视网膜神经变性越来越被假设为与血管改变相关,并且与DR发病机制有关。最近在人类和动物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结构和功能证据表明视网膜神经变性是DR的早期成分[16]。
神经元的存活、生长和功能取决于神经保护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平衡,神经保护因子的失衡被认为是糖尿病过程中导致视网膜神经变性的主要因素[17]。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视网膜中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EDF)、生长抑素(SST)、间质视黄醇结合蛋白(IRBP)、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和神经生长因子(NGF)等具有神经保护特性的视网膜因子浓度和功效降低[17]。PEDF和SST的主要来源是RPE细胞,两者都具有抗血管生成和神经保护特性,在视网膜稳态中具有关键作用[18-19]。PEDF具有防止氧化应激和谷氨酸兴奋毒性的作用[20]。人类视网膜SST的下调发生在DR早期阶段,并与视网膜神经变性相关[21]。IRBP是由光感受器产生的糖蛋白并参与视觉循环,IRBP对于脂肪酸转运以及光感受器的维持很重要。在DR的早期阶段,糖尿病供体的视网膜中IRBP呈低表达,并且这种表达下调与视网膜神经变性相关[22]。BDNF和NGF主要由胶质细胞和小神经胶质细胞合成和分泌。BDNF为视网膜神经元和无长突细胞提供营养支持。恢复NGF水平可防止神经元死亡的早期凋亡[23-25]。除了视网膜产生的天然神经保护因子的下调外,糖尿病视网膜中还存在VEGF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等神经营养因子和存活因子的上调[19]。VEGF在糖尿病黄斑水肿和新生血管形成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VEGF的过度表达伴随着神经保护因子的下调,尤其是PEDF[26]。神经保护因子合成的不平衡是DRN的早期和关键现象,这些发现具有临床意义,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2 DRN临床检测方法
频域OCT是精确且具有高度可重复性的检测工具[27]。多个横断面研究已经使用OCT评估了糖尿病患者中的神经解剖学改变;其发现,与正常组相比,非DR的糖尿病患眼中神经节细胞复合体层、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NFL)厚度降低[28]。这表明糖尿病患者的神经视网膜早期损伤发生在糖尿病血管变化之前并且独立于糖尿病血管变化。
OCT血管成像(OCTA)能够量化黄斑和视盘中的神经结构及其相应的血液供应。目前已被广泛用于评估青光眼及其他视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Lévêque等[29]观察发现,与正常人相比,青光眼患者的视神经乳头区(ONH)血管密度降低了20%~25%;同时ONH血管密度降低与视野损害以及视盘OCT中RNFL厚度降低相关。Cao等[30]研究发现,无临床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视盘周围RNFL厚度和血管分布密度显著降低。OCTA提供了较为精确测量量化视盘周围灌注的方法。
多焦ERG(mfERG)可记录视网膜多个区域神经元引起的场电位的变化。大量电生理研究发现无DR患眼mfERG振幅降低、潜伏时间延迟,视网膜功能障碍[31]。对于DR患者,mfERG基线潜伏时间异常的区域中发生新的视网膜病变的相对风险是无异常区域的21倍[28]。mfERG的改变表明神经功能障碍与DR血管异常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提示电生理的改变可以预测早期微血管异常的发展[32-33]。
3 DRN的治疗意义
基于神经保护的治疗,开辟预防或阻止DR发展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在DR发展过程中,神经保护的机制是除保护神经元丢失之外,也可减少由神经变性引起的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的破坏。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机制进行。
神经保护因子的失衡被认为是视网膜神经变性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些分子对于各种视网膜细胞的生长、分化和维持以及神经血管耦合非常重要。PEDF、SST以及NGF在DR动物实验中已被证实具有视神经保护作用[9]。玻璃体内注射PEDF可预防DR早期神经元紊乱和血管通透性过高[34]。PEDF还可以发挥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减少DR模型中的氧化应激和炎症标志物的产生[35]。SST可以控制视网膜中谷氨酸的释放,局部给予SST可预防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神经变性[36]。在此基础上正在进行多中心Ⅱ、Ⅲ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估局部施用SST滴眼剂以预防或阻止视网膜神经变性的功效[17]。NGF的眼内注射可以防止RGC和Müller细胞的凋亡以及周细胞丢失和无细胞毛细血管的形成。最近研究报道,NGF作为滴眼剂的应用可以保护RGC免于实验性青光眼或DR模型的变性[37]。
视网膜具有高代谢和高需氧的特点,因此特别容易受到血流受损引起的缺氧的影响[38]。这种血管反应的丧失可能使视网膜缺乏所需的氧气和葡萄糖,使神经元处于危险之中并导致视网膜病变。功能性缺血的改善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治疗靶点。在这方面已有研究证明,用全身给予氨基胍阻断诱导型NO合酶可以恢复糖尿病患眼视网膜中闪烁诱发的血管舒张[39]。
由于谷氨酸的细胞外积累在视网膜神经元死亡中起关键作用,因此降低谷氨酸水平的治疗似乎是合适的。在这方面,靶向谷氨酸受体的物质,例如美金刚已经显示出对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神经变性和血管异常具有有益作用[40]。有研究发现,STZ诱导的糖尿病小鼠模型用美金刚治疗3周后,其ERG a、b波振幅改善;长期给药也有利于减轻玻璃体视网膜VEGF水平升高,改善BRB完整性,并使RGC计数增加近16%[41]。但有关美金刚是否可能在糖尿病患眼的视网膜中发挥神经保护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神经变性是DR发病机制中的早期事件。因此,基于神经保护作为治疗DR早期阶段的新的和有针对性的方法提出治疗策略是合理的。然而,在这些阶段,患者实际上是无症状的。因此,诸如玻璃体内注射的积极治疗是不合适的。近年来的实验证据表明,许多药物可以通过滴眼液的方式使药理浓度到达视网膜[42]。同时局部给药可限制其对眼睛的作用,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相关的全身作用,从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43]。因此,需要多学科合作努力来设计一套关于眼科疾病中神经保护的实验和临床研究的指南。关于如何设计和执行转化研究的共识将优化资源的使用并促进有效神经保护剂的开发。
4 小结
目前研究表明,糖尿病能引起视网膜微血管病变和视网膜神经变性,这些事件随着视网膜NVU的逐渐破坏而合并。神经胶质功能障碍在糖尿病引起的神经血管偶联损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微血管疾病的早期发展。然而,我们关于将视网膜神经变性和微血管疾病联系起来的细胞和分子机制的知识仍然有限,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了解糖尿病患者NVU中复杂的细胞间动力学,阐明DRN与DR之间的时间关系以及如何延迟DRN的机制。同时,在临床工作中,建议评估和观察无DR的糖尿病患者早期视网膜神经结构及功能的变化,筛查视网膜神经功能障碍对于DR患者是否需要神经保护治疗至关重要。目前临床对DR的治疗主要集中在视网膜结构和视力已经受到影响的晚期阶段。更清楚地了解神经血管损伤的发病机制以及DRN在DR中的作用可能会提供新的和更有效的预防策略。
糖尿病视网膜神经变性(DRN)是在高血糖环境中由于多因素共同作用,包括氧化应激、微血管损伤、代谢紊乱、神经营养因子失衡和免疫损伤等造成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NVU)的正常功能受损,尤其是周细胞的丢失;NVU的逐渐破坏最终表现为临床上可识别的视网膜病变的迹象。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实验模型的研究表明,周细胞脱落发生在内皮细胞丢失之前。周细胞的损失损害了毛细血管的完整性,并导致血视网膜屏障(BRB)和血管渗漏增强。因此,视网膜神经变性越来越被假设为与血管改变相关,并且与DR发病机制有关。目前对DR的管理主要集中在视网膜结构和视力已经受到影响的晚期阶段;而一旦视网膜病变临床可见,视网膜损害很难逆转且DR进展的风险增加。因此,更深入地了解神经血管损伤的发病机制可能会为DR提供新的和更有效的预防策略。现针对DRN的发病机制、临床检测方法及治疗意义作一综述。
1 发病机制
视网膜是由三级神经元通过突触构成神经视网膜和RPE细胞相互连接形成[1]。光直接刺激的神经元是光感受器细胞,主要包括视杆、视锥细胞;来自视杆、视锥细胞的神经信号经历视网膜的其他神经元处理,以RGC中动作电位的形式输出,其轴突形成视神经[2]。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视网膜从双重血液供应中获得氧气,双循环的存在使视网膜氧合作用比较特别[3]。光感受器和外丛状层的较大部分间接地从脉络膜毛细血管中获得营养,而内层视网膜由视网膜中央动脉分支形成的浅表和深毛细血管丛供应。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光刺激选择性地提高内部视网膜层中细胞的代谢需求,导致视网膜血管扩张,而呼吸100%氧气导致它们收缩[4]。视网膜中氧气供应和消耗之间的微妙失衡使视网膜处于缺血性损伤风险中,视网膜内层对缺氧刺激的敏感性最高[5]。现在大多认为视网膜缺血在DR中起主要作用。据报道,RGC对急性、短暂和轻度全身性低氧应激以及糖尿病中发生的神经退行性过程高度敏感[6]。细胞功能障碍与生化改变相结合,如高血糖假性缺氧、蛋白激酶C途径活化、氧化应激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的增加被认为会引发炎症级联,引起视网膜损伤[7]。
视网膜“神经血管单位”包括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基底膜和视网膜血管元件(内皮细胞、周细胞)之间错综复杂的功能耦合和相互依赖性[8]。对维持血视网膜内屏障(IBRB)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同时动态根据代谢需求调节血流量[9]。由紧密连接复合物组成的IBRB对于调节血管腔和神经视网膜之间的代谢物交换有重要作用,维持了神经元功能所需的适当环境。而在糖尿病高血糖环境中,多种因素影响视网膜的完整神经血管单元,导致神经炎症、神经胶质细胞增生或激活;视网膜神经变性在视网膜显著血管病变之前发生[10]。神经变性的标志是神经细胞凋亡和神经胶质功能障碍,而BRB破坏、血管退化和微血管血流动力学反应改变(神经血管耦合受损)是早期微血管异常的主要特征。在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环境中,先天性免疫系统的早期激活,补体系统和微小的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引起神经元谷氨酸能和多巴胺能神经递质信号传导的改变,降低突触蛋白表达,改变神经胶质功能[11-13]。谷氨酸的积累和神经保护因子的丧失引发VEGF的激活,这在BRB破坏中起关键作用。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的逐渐破坏最终表现为临床上可识别的视网膜病变的迹象,尤其是周细胞损失。有关DR模型的实验研究表明,周细胞脱落发生在内皮细胞丢失之前[14]。周细胞的损失损害了毛细血管的完整性,并导致BRB的逐渐破坏和血管通透性增加[15]。Müller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等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的反应性进一步增加。细胞黏附分子在视网膜脉管系统上的上调导致循环单核细胞的白细胞增多和浸润增加,损害视网膜组织的神经毒素和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增多。进而出现临床上可见的微动脉瘤、出血以及视网膜组织中脂质渗出物的渗漏和功能性毛细血管的丧失,导致视力损害。若不及时治疗,DR进展到增生期,包括新生血管形成、黄斑水肿、玻璃体积血和瘢痕组织形成,最终导致失明。神经元和神经胶质功能障碍的丧失参与BRB破坏,血管反应和神经血管耦合受损,从而导致微血管病变和神经变性。因此,视网膜神经变性越来越被假设为与血管改变相关,并且与DR发病机制有关。最近在人类和动物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结构和功能证据表明视网膜神经变性是DR的早期成分[16]。
神经元的存活、生长和功能取决于神经保护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平衡,神经保护因子的失衡被认为是糖尿病过程中导致视网膜神经变性的主要因素[17]。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视网膜中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EDF)、生长抑素(SST)、间质视黄醇结合蛋白(IRBP)、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和神经生长因子(NGF)等具有神经保护特性的视网膜因子浓度和功效降低[17]。PEDF和SST的主要来源是RPE细胞,两者都具有抗血管生成和神经保护特性,在视网膜稳态中具有关键作用[18-19]。PEDF具有防止氧化应激和谷氨酸兴奋毒性的作用[20]。人类视网膜SST的下调发生在DR早期阶段,并与视网膜神经变性相关[21]。IRBP是由光感受器产生的糖蛋白并参与视觉循环,IRBP对于脂肪酸转运以及光感受器的维持很重要。在DR的早期阶段,糖尿病供体的视网膜中IRBP呈低表达,并且这种表达下调与视网膜神经变性相关[22]。BDNF和NGF主要由胶质细胞和小神经胶质细胞合成和分泌。BDNF为视网膜神经元和无长突细胞提供营养支持。恢复NGF水平可防止神经元死亡的早期凋亡[23-25]。除了视网膜产生的天然神经保护因子的下调外,糖尿病视网膜中还存在VEGF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等神经营养因子和存活因子的上调[19]。VEGF在糖尿病黄斑水肿和新生血管形成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VEGF的过度表达伴随着神经保护因子的下调,尤其是PEDF[26]。神经保护因子合成的不平衡是DRN的早期和关键现象,这些发现具有临床意义,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2 DRN临床检测方法
频域OCT是精确且具有高度可重复性的检测工具[27]。多个横断面研究已经使用OCT评估了糖尿病患者中的神经解剖学改变;其发现,与正常组相比,非DR的糖尿病患眼中神经节细胞复合体层、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NFL)厚度降低[28]。这表明糖尿病患者的神经视网膜早期损伤发生在糖尿病血管变化之前并且独立于糖尿病血管变化。
OCT血管成像(OCTA)能够量化黄斑和视盘中的神经结构及其相应的血液供应。目前已被广泛用于评估青光眼及其他视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Lévêque等[29]观察发现,与正常人相比,青光眼患者的视神经乳头区(ONH)血管密度降低了20%~25%;同时ONH血管密度降低与视野损害以及视盘OCT中RNFL厚度降低相关。Cao等[30]研究发现,无临床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视盘周围RNFL厚度和血管分布密度显著降低。OCTA提供了较为精确测量量化视盘周围灌注的方法。
多焦ERG(mfERG)可记录视网膜多个区域神经元引起的场电位的变化。大量电生理研究发现无DR患眼mfERG振幅降低、潜伏时间延迟,视网膜功能障碍[31]。对于DR患者,mfERG基线潜伏时间异常的区域中发生新的视网膜病变的相对风险是无异常区域的21倍[28]。mfERG的改变表明神经功能障碍与DR血管异常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提示电生理的改变可以预测早期微血管异常的发展[32-33]。
3 DRN的治疗意义
基于神经保护的治疗,开辟预防或阻止DR发展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在DR发展过程中,神经保护的机制是除保护神经元丢失之外,也可减少由神经变性引起的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的破坏。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机制进行。
神经保护因子的失衡被认为是视网膜神经变性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些分子对于各种视网膜细胞的生长、分化和维持以及神经血管耦合非常重要。PEDF、SST以及NGF在DR动物实验中已被证实具有视神经保护作用[9]。玻璃体内注射PEDF可预防DR早期神经元紊乱和血管通透性过高[34]。PEDF还可以发挥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减少DR模型中的氧化应激和炎症标志物的产生[35]。SST可以控制视网膜中谷氨酸的释放,局部给予SST可预防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神经变性[36]。在此基础上正在进行多中心Ⅱ、Ⅲ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估局部施用SST滴眼剂以预防或阻止视网膜神经变性的功效[17]。NGF的眼内注射可以防止RGC和Müller细胞的凋亡以及周细胞丢失和无细胞毛细血管的形成。最近研究报道,NGF作为滴眼剂的应用可以保护RGC免于实验性青光眼或DR模型的变性[37]。
视网膜具有高代谢和高需氧的特点,因此特别容易受到血流受损引起的缺氧的影响[38]。这种血管反应的丧失可能使视网膜缺乏所需的氧气和葡萄糖,使神经元处于危险之中并导致视网膜病变。功能性缺血的改善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治疗靶点。在这方面已有研究证明,用全身给予氨基胍阻断诱导型NO合酶可以恢复糖尿病患眼视网膜中闪烁诱发的血管舒张[39]。
由于谷氨酸的细胞外积累在视网膜神经元死亡中起关键作用,因此降低谷氨酸水平的治疗似乎是合适的。在这方面,靶向谷氨酸受体的物质,例如美金刚已经显示出对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神经变性和血管异常具有有益作用[40]。有研究发现,STZ诱导的糖尿病小鼠模型用美金刚治疗3周后,其ERG a、b波振幅改善;长期给药也有利于减轻玻璃体视网膜VEGF水平升高,改善BRB完整性,并使RGC计数增加近16%[41]。但有关美金刚是否可能在糖尿病患眼的视网膜中发挥神经保护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神经变性是DR发病机制中的早期事件。因此,基于神经保护作为治疗DR早期阶段的新的和有针对性的方法提出治疗策略是合理的。然而,在这些阶段,患者实际上是无症状的。因此,诸如玻璃体内注射的积极治疗是不合适的。近年来的实验证据表明,许多药物可以通过滴眼液的方式使药理浓度到达视网膜[42]。同时局部给药可限制其对眼睛的作用,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相关的全身作用,从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43]。因此,需要多学科合作努力来设计一套关于眼科疾病中神经保护的实验和临床研究的指南。关于如何设计和执行转化研究的共识将优化资源的使用并促进有效神经保护剂的开发。
4 小结
目前研究表明,糖尿病能引起视网膜微血管病变和视网膜神经变性,这些事件随着视网膜NVU的逐渐破坏而合并。神经胶质功能障碍在糖尿病引起的神经血管偶联损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微血管疾病的早期发展。然而,我们关于将视网膜神经变性和微血管疾病联系起来的细胞和分子机制的知识仍然有限,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了解糖尿病患者NVU中复杂的细胞间动力学,阐明DRN与DR之间的时间关系以及如何延迟DRN的机制。同时,在临床工作中,建议评估和观察无DR的糖尿病患者早期视网膜神经结构及功能的变化,筛查视网膜神经功能障碍对于DR患者是否需要神经保护治疗至关重要。目前临床对DR的治疗主要集中在视网膜结构和视力已经受到影响的晚期阶段。更清楚地了解神经血管损伤的发病机制以及DRN在DR中的作用可能会提供新的和更有效的预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