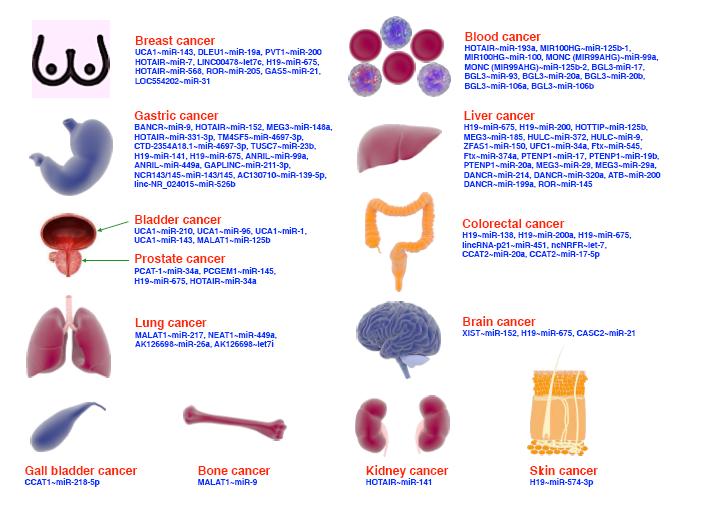引用本文: 胡玉章, 周抒, 刘华, 周波, 陈艳君. 后巩膜炎误诊三例.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0, 36(6): 471-473.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191120-00383 复制
版权信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期刊社《中华眼底病杂志》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改编
例1 患者女,63岁。头痛伴双眼先后疼痛1个月于2019年5月14日至成都爱迪眼科医院就诊。患者既往高血压病史多年。2019年4月25日患者不明原因眩晕跌倒持续约30 s,伴头痛、眼痛。外院CT检查未见异常,以晕厥、意识丧失、头痛收入神经内科。住院期间血压正常。因眼痛加重,眼科会诊疑诊左眼巩膜炎,眼B型超声检查,增益105 dB,未见异常(图1)。实验室检查结果未见异常。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左眼视力0.4;均不能矫正。左眼穹隆结膜轻度充血;眼球各方运动良好,疼痛明显。双眼眼前节及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OCT检查未见异常。B型超声检查,增益88 dB,双眼“T”形征(图2)。实验室检查,红细胞沉降率(ESR)130 mm/h,C-反应蛋白(CRP)阳性。诊断:双眼后巩膜炎。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1周后眼痛、头部不适症状完全消失。治疗后3个月,双眼视力均为0.8;后巩膜厚度下降,接近正常。ESR16 mm/h,CRP阴性。TORCH检查,抗单疱病毒Ⅰ/Ⅱ抗体IgM 4.83(正常值<0.90)。给予阿昔洛韦口服。
 图1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1A、1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105 dB,双眼未见异常
图1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1A、1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105 dB,双眼未见异常
 图2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2A、2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88 dB,双眼“T”形征
图2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2A、2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88 dB,双眼“T”形征
例2 患者女,34岁。因左眼眼前遮挡感伴视力下降9 d于2019年2月8日至成都爱迪眼科医院就诊。患者3年前不明原因右眼充血、结膜水肿,当地医院诊断结膜炎,给予抗生素眼液治疗无效;后因症状逐渐加重伴眼球转动痛,再次给予抗生素、糖皮质激素静脉滴注20余天后好转。8个月前出现双眼干涩不适,左眼疼痛,当地医院给予氟米龙、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滴眼治疗无效。其后症状逐渐加重,结膜水肿,视野正中出现暗影,视力下降。6个月前右眼出现疼痛,充血,当地医院给予静脉滴注葛根素,治疗3 d后视力下降。
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05,矫正0.6;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02。双眼屈光间质透明。右眼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左眼黄斑区稍模糊,反光弥散,视网膜未见出血、水肿。2019年2月10日自觉右眼视力下降伴眼球疼痛,转动更重。检查,右眼视力0.12,矫正1.0;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02。双眼眼压19 mmHg(1 mmHg=0.133 kPa)。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疼痛感明显。球结膜水肿,眼前节未见异常。右眼视盘上方视网膜局限性水肿、隆起、渗出性视网膜脱离,未见出血(图3A)。左眼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B型超声检查,右眼局限性巩膜增厚,浆液性视网膜脱离;左眼后巩膜弥散性增厚(图3B,3C)。FFA检查,右眼早期视盘上方针尖样荧光素渗漏,晚期大片荧光蓄积;左眼晚期未见异常荧光素渗漏,视盘荧光蓄积,背景斑驳样荧光(图3D,3E)。实验室检查,ESR 33 mm/h,CRP阳性。诊断:右眼结节性后巩膜炎;左眼后巩膜炎。
 图3
例2患者无赤光眼底、B型超声、FFA像。3A示右眼无赤光眼底像,视盘鼻上方局限性水肿、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红箭)。3B、3C分别示右眼、左眼B型超声像。右眼视盘上方巩膜脉络膜局限性增厚,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红箭);左眼巩膜弥漫性增厚,筋膜囊水肿与视神经无回声区相连,呈“T”形。3D、3E分别示右眼、左眼FFA晚期像。右眼视盘上方局限性大量荧光蓄积,呈多湖样变;左眼视盘荧光蓄积,背景斑驳样荧光
图3
例2患者无赤光眼底、B型超声、FFA像。3A示右眼无赤光眼底像,视盘鼻上方局限性水肿、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红箭)。3B、3C分别示右眼、左眼B型超声像。右眼视盘上方巩膜脉络膜局限性增厚,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红箭);左眼巩膜弥漫性增厚,筋膜囊水肿与视神经无回声区相连,呈“T”形。3D、3E分别示右眼、左眼FFA晚期像。右眼视盘上方局限性大量荧光蓄积,呈多湖样变;左眼视盘荧光蓄积,背景斑驳样荧光
明确诊断后,给予口服醋酸泼尼松50 mg,1次/d,连续7 d后减量。治疗后14 d,双眼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右眼视盘上方水肿、隆起明显减轻。继续前述治疗。1个半月后,右眼视力0.08,矫正1.0;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15。双眼眼压正常。自述症状消失。B型超声检查可见巩膜厚度变薄,基本恢复正常。3个月后,患者自行停药右眼再次出现红、转动疼痛。右眼视力0.1,矫正0.6;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2。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7.7、20.0 mmHg。右眼结膜充血、颞侧结膜水肿。B型超声检查可见后巩膜增厚。继续糖皮质激素治疗。5个月后,右眼视力0.08,矫正1.0;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3。眼压正常。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口服醋酸泼尼松10 mg,1次/d。6个月后。右眼视力0.06,矫正1.0;左眼视力0.02,矫正0.6。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无疼痛。眼底未见异常。停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例3 患者女,27岁。因双眼疼痛、左眼上斜视3个月于2018年3月2日至成都爱迪眼科医院就诊。6年前反复发生双眼上眼睑水肿、眼痛,以右眼为著。当地医院给予治疗(具体不详)后症状无明显好转。5年前出现右眼球突出,转动受限,外院诊断右眼间歇性外斜,行右眼斜视矫正手术。
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5,-0.75-0.50×100→1.0;左眼视力0.6,-2.75DC×85→1.0。双眼眼前节、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双眼中心凹注视。左眼内转受限。诊断:左眼限制性外斜视。行左眼外直肌徙后术。手术后左眼内转正常,眼位正位。手术后14 d,患者再次出现双眼眼睑水肿,眼痛。右眼颞侧结膜明显水肿,左眼结膜轻度水肿;双眼结膜无充血。双眼眼前节及右眼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左眼视盘上下沿水肿,视网膜脉络膜皱褶。B型超声检查,右眼未见异常;左眼后巩膜局限性增厚,巩膜下积液(图4A)。给予全身静脉滴注头孢唑林2 g,2次/d,连续2 d;口服头孢克肟0.1 g,2次/d,醋酸泼尼松30 mg/d,清晨顿服;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滴眼。治疗后10 d至外院就诊,诊断为左眼眶非特异性炎症。CT检查,左侧眼环外侧份外壁局限性增厚;外直肌肌止端增厚(图4B,4C)。给予静脉滴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1000 mg,连续3 d,其后改为地塞米松磷酸钠10 mg。醋酸泼尼松 40 mg/d,清晨顿服,7 d后减为10 mg。自诉左眼眶疼痛减轻,外转受限好转。2019年9月10日患者再次出现左眼痛,不能外转。实验室检查,ESR 22 mm/h,CRP阴性。综合全部病史和治疗过程,并结合检查结果,诊断:左眼结节型后巩膜炎(复发)。给予以口服醋酸泼尼松60 mg/d,清晨顿服。治疗后7 d复查,右眼视力0.3,矫正0.8;左眼视力0.3,矫正1.0。左眼运动仅轻度受限,疼痛消失。眼底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ESR17 mm/h,CRP阴性;免疫全套、TORCH检查未见异常。37 d后复查,双眼矫正视力1.0。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无复视。眼前节、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CT检查,双眼眼环形态完整,左眼外侧壁增厚消失。实验室检查,ESR、CRP、血常规均正常。醋酸泼尼松逐渐减量至3个月后停用。
 图4
例3患者B型超声、眼眶CT像。4A示B型超声像,左眼玻璃体暗区少量点状弱回声,眼球后壁见实性隆起(白箭),球后低回声区,其下有积液;4B示眼眶CT冠状位像,左眼眼环外侧、外直肌附着处增厚(黑箭);4C示眼眶CT水平位像,左眼外侧份局限性增厚(白箭)
图4
例3患者B型超声、眼眶CT像。4A示B型超声像,左眼玻璃体暗区少量点状弱回声,眼球后壁见实性隆起(白箭),球后低回声区,其下有积液;4B示眼眶CT冠状位像,左眼眼环外侧、外直肌附着处增厚(黑箭);4C示眼眶CT水平位像,左眼外侧份局限性增厚(白箭)
讨论 后巩膜炎是指锯齿缘或直肌附着点之后的巩膜炎症,可伴或不伴前部巩膜炎。病因包括自身免疫反应和感染[1]。因其发病率相对较低,而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常导致误诊或漏诊[1-6]。本病好发于中年女性,偶可见儿童后巩膜炎病例[3]。
本文3例均为女性。例1患者外院初诊时由于病史采集错误,导致此后检查未能找到病因,诊断不明。眼科会诊时怀疑后巩膜炎,但由于B型超声检查时参数使用不当,眼球后段呈强回声,未能明确诊断。例2患者双眼先后出现眼球疼痛,反复发作3年。期间错误的诊断、不规范治疗,使得病情更为复杂。右眼再次急性发病时,B型超声检查见右眼典型局灶性巩膜脉络膜增厚、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左眼典型“T”形征方明确诊断。例3患者病史较长,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的滥用,使得疾病表现更加错综复杂。后巩膜炎波及到眼外肌肌止端,导致眼球运动障碍、前突。由于对该病的认识不够,双眼均施行了不必要的手术。左眼再次出现眼痛、外转不能时,仅使用糖皮质激素1周,眼球外转运动即基本恢复。末次随访时双眼眼球运动恢复正常,症状完全消失。本文3例患者均由于前期诊断不明,治疗不规范且盲目以及糖皮质激素治疗时间不够,减量、停药过快而导致病情反复。
后巩膜炎B型超声较有特征,表现为后部巩膜弥漫型或结节型增厚,炎症导致球后筋膜囊水肿时其低回声区可与视神经无回声区相连,呈“T”形征[7],是诊断后巩膜炎的有效检查手段。但需注意的是检查时应选用恰当的增益参数,本文例1患者曾疑似后巩膜炎,但检查时不恰当使用最高增益参数,导致分辨率不够,眼球后段呈强回声,影像表现为白色反光,因而未能明确诊断。FFA可用于鉴别诊断,本文例2患者右眼FFA早期脉络膜针尖样荧光素渗漏,晚期局部荧光蓄积,多湖样变,类似Vogt-小柳-原田综合征(VKH综合征)影像表现。但病灶局限,前房、玻璃体透明;无头晕、耳鸣、重听等全身表现。可加以鉴别。CT和MRI检查也有一定帮助,可检测巩膜厚度。
后巩膜炎治疗以全身糖皮质激素抗炎为主,正规、小剂量、足够疗程治疗。多数患者能获得良好治疗效果;反复发作的少数患者需全身加用免疫抑制剂。眼局部用药效果较差。治疗后多数患者脉络膜皱褶和视网膜下液可完全消退;少数患者脉络膜皱褶和巩膜增厚可持续较长时间。
本病需主要与脉络膜炎、VKH综合征、慢性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等鉴别。后巩膜炎以明显眼痛、转动痛为主要症状,无眼内炎症或非常轻微;结节性后巩膜炎导致局灶性脉络膜荧光素渗漏、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容易与VKH综合征混淆。但上述疾病基本不会出现眼球疼痛或疼痛非常轻微;眼内炎症表现和伴发的全身情况更为明显。另外,准确的B型超声检查也可以很好鉴别。
例1 患者女,63岁。头痛伴双眼先后疼痛1个月于2019年5月14日至成都爱迪眼科医院就诊。患者既往高血压病史多年。2019年4月25日患者不明原因眩晕跌倒持续约30 s,伴头痛、眼痛。外院CT检查未见异常,以晕厥、意识丧失、头痛收入神经内科。住院期间血压正常。因眼痛加重,眼科会诊疑诊左眼巩膜炎,眼B型超声检查,增益105 dB,未见异常(图1)。实验室检查结果未见异常。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左眼视力0.4;均不能矫正。左眼穹隆结膜轻度充血;眼球各方运动良好,疼痛明显。双眼眼前节及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OCT检查未见异常。B型超声检查,增益88 dB,双眼“T”形征(图2)。实验室检查,红细胞沉降率(ESR)130 mm/h,C-反应蛋白(CRP)阳性。诊断:双眼后巩膜炎。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1周后眼痛、头部不适症状完全消失。治疗后3个月,双眼视力均为0.8;后巩膜厚度下降,接近正常。ESR16 mm/h,CRP阴性。TORCH检查,抗单疱病毒Ⅰ/Ⅱ抗体IgM 4.83(正常值<0.90)。给予阿昔洛韦口服。
 图1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1A、1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105 dB,双眼未见异常
图1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1A、1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105 dB,双眼未见异常
 图2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2A、2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88 dB,双眼“T”形征
图2
例1患者双眼B型超声像。2A、2B分别示右眼、左眼。增益88 dB,双眼“T”形征
例2 患者女,34岁。因左眼眼前遮挡感伴视力下降9 d于2019年2月8日至成都爱迪眼科医院就诊。患者3年前不明原因右眼充血、结膜水肿,当地医院诊断结膜炎,给予抗生素眼液治疗无效;后因症状逐渐加重伴眼球转动痛,再次给予抗生素、糖皮质激素静脉滴注20余天后好转。8个月前出现双眼干涩不适,左眼疼痛,当地医院给予氟米龙、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滴眼治疗无效。其后症状逐渐加重,结膜水肿,视野正中出现暗影,视力下降。6个月前右眼出现疼痛,充血,当地医院给予静脉滴注葛根素,治疗3 d后视力下降。
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05,矫正0.6;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02。双眼屈光间质透明。右眼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左眼黄斑区稍模糊,反光弥散,视网膜未见出血、水肿。2019年2月10日自觉右眼视力下降伴眼球疼痛,转动更重。检查,右眼视力0.12,矫正1.0;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02。双眼眼压19 mmHg(1 mmHg=0.133 kPa)。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疼痛感明显。球结膜水肿,眼前节未见异常。右眼视盘上方视网膜局限性水肿、隆起、渗出性视网膜脱离,未见出血(图3A)。左眼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B型超声检查,右眼局限性巩膜增厚,浆液性视网膜脱离;左眼后巩膜弥散性增厚(图3B,3C)。FFA检查,右眼早期视盘上方针尖样荧光素渗漏,晚期大片荧光蓄积;左眼晚期未见异常荧光素渗漏,视盘荧光蓄积,背景斑驳样荧光(图3D,3E)。实验室检查,ESR 33 mm/h,CRP阳性。诊断:右眼结节性后巩膜炎;左眼后巩膜炎。
 图3
例2患者无赤光眼底、B型超声、FFA像。3A示右眼无赤光眼底像,视盘鼻上方局限性水肿、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红箭)。3B、3C分别示右眼、左眼B型超声像。右眼视盘上方巩膜脉络膜局限性增厚,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红箭);左眼巩膜弥漫性增厚,筋膜囊水肿与视神经无回声区相连,呈“T”形。3D、3E分别示右眼、左眼FFA晚期像。右眼视盘上方局限性大量荧光蓄积,呈多湖样变;左眼视盘荧光蓄积,背景斑驳样荧光
图3
例2患者无赤光眼底、B型超声、FFA像。3A示右眼无赤光眼底像,视盘鼻上方局限性水肿、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红箭)。3B、3C分别示右眼、左眼B型超声像。右眼视盘上方巩膜脉络膜局限性增厚,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红箭);左眼巩膜弥漫性增厚,筋膜囊水肿与视神经无回声区相连,呈“T”形。3D、3E分别示右眼、左眼FFA晚期像。右眼视盘上方局限性大量荧光蓄积,呈多湖样变;左眼视盘荧光蓄积,背景斑驳样荧光
明确诊断后,给予口服醋酸泼尼松50 mg,1次/d,连续7 d后减量。治疗后14 d,双眼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右眼视盘上方水肿、隆起明显减轻。继续前述治疗。1个半月后,右眼视力0.08,矫正1.0;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15。双眼眼压正常。自述症状消失。B型超声检查可见巩膜厚度变薄,基本恢复正常。3个月后,患者自行停药右眼再次出现红、转动疼痛。右眼视力0.1,矫正0.6;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2。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7.7、20.0 mmHg。右眼结膜充血、颞侧结膜水肿。B型超声检查可见后巩膜增厚。继续糖皮质激素治疗。5个月后,右眼视力0.08,矫正1.0;左眼视力数指,矫正0.3。眼压正常。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口服醋酸泼尼松10 mg,1次/d。6个月后。右眼视力0.06,矫正1.0;左眼视力0.02,矫正0.6。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无疼痛。眼底未见异常。停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例3 患者女,27岁。因双眼疼痛、左眼上斜视3个月于2018年3月2日至成都爱迪眼科医院就诊。6年前反复发生双眼上眼睑水肿、眼痛,以右眼为著。当地医院给予治疗(具体不详)后症状无明显好转。5年前出现右眼球突出,转动受限,外院诊断右眼间歇性外斜,行右眼斜视矫正手术。
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5,-0.75-0.50×100→1.0;左眼视力0.6,-2.75DC×85→1.0。双眼眼前节、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双眼中心凹注视。左眼内转受限。诊断:左眼限制性外斜视。行左眼外直肌徙后术。手术后左眼内转正常,眼位正位。手术后14 d,患者再次出现双眼眼睑水肿,眼痛。右眼颞侧结膜明显水肿,左眼结膜轻度水肿;双眼结膜无充血。双眼眼前节及右眼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左眼视盘上下沿水肿,视网膜脉络膜皱褶。B型超声检查,右眼未见异常;左眼后巩膜局限性增厚,巩膜下积液(图4A)。给予全身静脉滴注头孢唑林2 g,2次/d,连续2 d;口服头孢克肟0.1 g,2次/d,醋酸泼尼松30 mg/d,清晨顿服;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滴眼。治疗后10 d至外院就诊,诊断为左眼眶非特异性炎症。CT检查,左侧眼环外侧份外壁局限性增厚;外直肌肌止端增厚(图4B,4C)。给予静脉滴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1000 mg,连续3 d,其后改为地塞米松磷酸钠10 mg。醋酸泼尼松 40 mg/d,清晨顿服,7 d后减为10 mg。自诉左眼眶疼痛减轻,外转受限好转。2019年9月10日患者再次出现左眼痛,不能外转。实验室检查,ESR 22 mm/h,CRP阴性。综合全部病史和治疗过程,并结合检查结果,诊断:左眼结节型后巩膜炎(复发)。给予以口服醋酸泼尼松60 mg/d,清晨顿服。治疗后7 d复查,右眼视力0.3,矫正0.8;左眼视力0.3,矫正1.0。左眼运动仅轻度受限,疼痛消失。眼底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ESR17 mm/h,CRP阴性;免疫全套、TORCH检查未见异常。37 d后复查,双眼矫正视力1.0。双眼眼球各方运动良好,无复视。眼前节、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CT检查,双眼眼环形态完整,左眼外侧壁增厚消失。实验室检查,ESR、CRP、血常规均正常。醋酸泼尼松逐渐减量至3个月后停用。
 图4
例3患者B型超声、眼眶CT像。4A示B型超声像,左眼玻璃体暗区少量点状弱回声,眼球后壁见实性隆起(白箭),球后低回声区,其下有积液;4B示眼眶CT冠状位像,左眼眼环外侧、外直肌附着处增厚(黑箭);4C示眼眶CT水平位像,左眼外侧份局限性增厚(白箭)
图4
例3患者B型超声、眼眶CT像。4A示B型超声像,左眼玻璃体暗区少量点状弱回声,眼球后壁见实性隆起(白箭),球后低回声区,其下有积液;4B示眼眶CT冠状位像,左眼眼环外侧、外直肌附着处增厚(黑箭);4C示眼眶CT水平位像,左眼外侧份局限性增厚(白箭)
讨论 后巩膜炎是指锯齿缘或直肌附着点之后的巩膜炎症,可伴或不伴前部巩膜炎。病因包括自身免疫反应和感染[1]。因其发病率相对较低,而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常导致误诊或漏诊[1-6]。本病好发于中年女性,偶可见儿童后巩膜炎病例[3]。
本文3例均为女性。例1患者外院初诊时由于病史采集错误,导致此后检查未能找到病因,诊断不明。眼科会诊时怀疑后巩膜炎,但由于B型超声检查时参数使用不当,眼球后段呈强回声,未能明确诊断。例2患者双眼先后出现眼球疼痛,反复发作3年。期间错误的诊断、不规范治疗,使得病情更为复杂。右眼再次急性发病时,B型超声检查见右眼典型局灶性巩膜脉络膜增厚、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左眼典型“T”形征方明确诊断。例3患者病史较长,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的滥用,使得疾病表现更加错综复杂。后巩膜炎波及到眼外肌肌止端,导致眼球运动障碍、前突。由于对该病的认识不够,双眼均施行了不必要的手术。左眼再次出现眼痛、外转不能时,仅使用糖皮质激素1周,眼球外转运动即基本恢复。末次随访时双眼眼球运动恢复正常,症状完全消失。本文3例患者均由于前期诊断不明,治疗不规范且盲目以及糖皮质激素治疗时间不够,减量、停药过快而导致病情反复。
后巩膜炎B型超声较有特征,表现为后部巩膜弥漫型或结节型增厚,炎症导致球后筋膜囊水肿时其低回声区可与视神经无回声区相连,呈“T”形征[7],是诊断后巩膜炎的有效检查手段。但需注意的是检查时应选用恰当的增益参数,本文例1患者曾疑似后巩膜炎,但检查时不恰当使用最高增益参数,导致分辨率不够,眼球后段呈强回声,影像表现为白色反光,因而未能明确诊断。FFA可用于鉴别诊断,本文例2患者右眼FFA早期脉络膜针尖样荧光素渗漏,晚期局部荧光蓄积,多湖样变,类似Vogt-小柳-原田综合征(VKH综合征)影像表现。但病灶局限,前房、玻璃体透明;无头晕、耳鸣、重听等全身表现。可加以鉴别。CT和MRI检查也有一定帮助,可检测巩膜厚度。
后巩膜炎治疗以全身糖皮质激素抗炎为主,正规、小剂量、足够疗程治疗。多数患者能获得良好治疗效果;反复发作的少数患者需全身加用免疫抑制剂。眼局部用药效果较差。治疗后多数患者脉络膜皱褶和视网膜下液可完全消退;少数患者脉络膜皱褶和巩膜增厚可持续较长时间。
本病需主要与脉络膜炎、VKH综合征、慢性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等鉴别。后巩膜炎以明显眼痛、转动痛为主要症状,无眼内炎症或非常轻微;结节性后巩膜炎导致局灶性脉络膜荧光素渗漏、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容易与VKH综合征混淆。但上述疾病基本不会出现眼球疼痛或疼痛非常轻微;眼内炎症表现和伴发的全身情况更为明显。另外,准确的B型超声检查也可以很好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