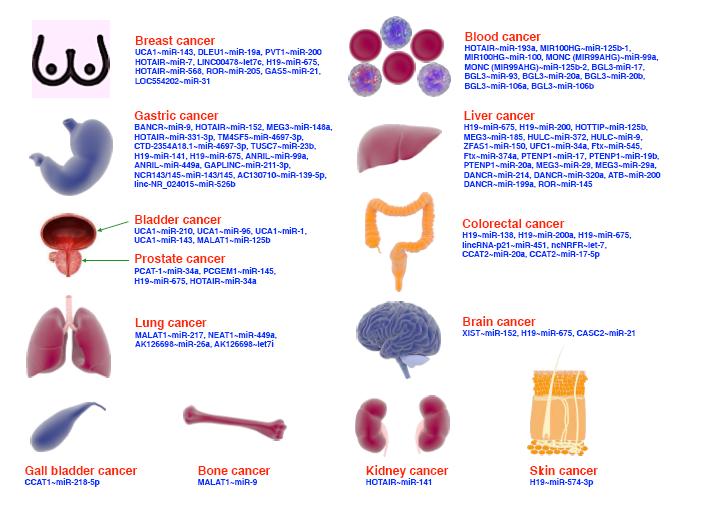疫苗相关性葡萄膜炎(VAU)是接种疫苗后发生的一种罕见的不良反应。VAU临床多表现为前葡萄膜炎,症状轻微且对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好,但其也可出现严重的后葡萄膜炎或全葡萄膜炎,如多发性一过性白点综合征、Vogt-Koyanagi-Harada综合征、急性后极部多灶性鳞状色素上皮病变等。VAU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主要包括疫苗Shoenfeld综合征、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的Ⅲ型超敏反应、减毒活疫苗的直接感染及分子拟态理论。VAU有一定的自限性,大多数患者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可自愈。未来在临床中建议对所有葡萄膜炎患者询问最近的疫苗接种史。对于灭活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接种史患者,应考虑发生Shoenfeld综合征的可能性,仔细寻找其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病史、体征及症状。
引用本文: 吴烁, 张川, 赵明威, 侯婧. 疫苗相关性葡萄膜炎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3, 39(9): 773-778.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20126-00046 复制
版权信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期刊社《中华眼底病杂志》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改编
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疾病是公共卫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疫苗接种使许多曾经广泛传播、严重或致命传染病的死亡率下降了90%以上[1]。但是,疫苗也可能带来各种副作用,几乎所有种类的疫苗都报道了疫苗相关性葡萄膜炎(VAU)。VAU为接种疫苗后发生的葡萄膜炎,是疫苗接种后一种罕见的不良反应。VAU十分罕见,迄今为止,文献中所报道的各种疫苗引起的VAU大约300例,其发病率为每100 000剂中有8~13剂[2]。VAU最常发生于接种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后(40.5%)[3],其次依次为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15.6%)[4]、流感病毒疫苗(9.7%)、卡介苗疫苗(7.3%)、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MMR)单独或联合疫苗(4.8%)、水痘病毒单独或联合疫苗(4.8%)和甲型肝炎病毒单独或联合疫苗(2.4%)[5]。VAU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平均发病年龄为30岁,从接种疫苗到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16 d[5]。VAU临床多表现为前葡萄膜炎,症状轻微且对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好[5]。但严重者可发生后葡萄膜炎或全葡萄膜炎,如多发性一过性白点综合征(MEWDS)、Vogt-Koyanagi-Harada综合征(VKH)和急性后极部多灶性鳞状色素上皮病变(APMPPE)等[5]。VAU常以视物模糊、眼痛、畏光、眼红为首发症状,可伴有中心暗点、视野缺失、色觉减退,偶见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碍。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结膜充血、角膜后沉着物(KP)、前房浮游细胞、前房闪辉、前玻璃体浮游细胞,严重者可出现前房积脓和虹膜后粘连。眼底检查示视盘水肿伴大量白色病变,偶见黄斑颗粒,长期可形成色素瘢痕。对于不同的并发症,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有不同的表现:当并发APMPPE时可表现为早期弱荧光,晚期强荧光;当并发MEWDS时可表现为早期斑点状强荧光,晚期荧光着染。临床医生需了解VAU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及诊疗建议,避免漏诊及盲目缩小患者疫苗接种适应证。现就VAU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VAU的发病机制
疫苗主要分为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及类毒素疫苗。疫苗的作用原理是注入抗原材料,激活免疫系统对特定病原体产生适应性免疫。但VAU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目前可能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1 疫苗Shoenfeld综合征
Shoenfeld综合征是指由疫苗佐剂(通常为铝盐)引起的自身炎症和免疫反应[6-8]。佐剂包括铝盐、氢氧化物、磷酸盐和硫酸钾。疫苗佐剂能够将免疫反应转变为更多的辅助性T细胞1(Th1)(CD4+)细胞免疫反应[9],从而节省剂量和诱导更快速、更广泛和更强的免疫反应[7-9]。但是,超过耐受机制的自身反应性T细胞可以被外源性佐剂触发成为自身攻击性细胞[10],从而诱发自身免疫或加重自身免疫性疾病。
铝盐是最常见的引发VAU的佐剂,纳米铝颗粒具有独特的跨越血脑屏障和诱导免疫性炎症反应的能力[11-12],在人体内的存续期长且会反复暴露,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和随后的慢性炎症[13]。Shoenfeld综合征常见的全身症状包括关节痛、肌痛和慢性疲劳[7-8],具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佐剂可以诱导免疫系统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随后在遗传易感个体中,自身反应性淋巴细胞的扩张可能会被有缺陷的调节细胞/回路进一步加速[14],继而导致炎症的发生。Shoenfeld综合征最常发生在接种流感病毒疫苗、HPV疫苗、百白破疫苗、MMR疫苗和卡介苗疫苗后[15]。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信使RNA(mRNA)疫苗中包含的佐剂通过包括Toll样受体在内的内溶质或细胞质核酸受体来刺激先天免疫[16],先天免疫系统的激活可导致细胞因子的显著激活,从而诱导葡萄膜炎的发生,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1.2 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的Ⅲ型超敏反应
接种疫苗后,在血液中循环的抗原与免疫应答产生的抗体形成循环免疫复合物,导致血管活性胺如5-羟色胺、组胺和血小板活化因子的释放,增加血管通透性,允许更大的免疫复合物在葡萄膜沉积[6, 17]。免疫复合物沉积后激活补体系统,导致白细胞趋化和组织肥大细胞脱颗粒[18],引起Ⅲ型超敏反应[3],组织损伤加重,引发葡萄膜炎。但是由于循环免疫复合物的特性和血房水屏障的存在,只有少数循环免疫复合物沉积的现象会导致VAU的发生,当合并有全身性免疫复合体疾病并伴有巩膜和角膜缘血液回流障碍时,由于这些无血管结构的营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管层,因此,免疫神经丛可能在角膜周围和巩膜坏死和溃疡等危险情况下发挥作用[18],导致接种疫苗后葡萄膜炎发生的概率增加。该机制下发生的VAU,大多能在房水中检测到循环免疫复合物[3]。研究报道,迟发型超敏反应也可能是VAU的发病机制之一[19]。
1.3 减毒活疫苗的直接感染
一部分VAU是由减毒活疫苗的活株诱导眼结构的直接感染所致[19]。Guex-Crosier等[20]假设卡介苗接种后眼部炎症的可能是由于分枝杆菌的直接感染。与这一理论相一致的是,Llorenç等[21]在体外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细胞模型中发现,卡介苗能够感染RPE细胞,并在细胞内复制直到细胞溶解,活化的RPE细胞具有巨噬细胞样的功能,可形成非干酪性肉芽肿。抗生素治疗的相对有效性是证实这一假设的另一个线索[5,19]。此外,卡介苗感染细胞48 h后细胞增生明显增强,卡介苗的这种促增生作用可以解释临床上观察到的部分患者的RPE增生[21]。另外,在带状疱疹疫苗不良反应报告中,也存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皮肤疱疹液及玻璃体液证实接种后特定病毒的持续复制[19]。
1.4 分子拟态理论及VAU与自身免疫病的关系
疫苗肽片段和葡萄膜自身肽之间的分子具有相似性。在接种疫苗后,机体针对减毒株产生的免疫反应可以与减毒株共享肽序列(或结构)的人类蛋白质(葡萄膜自身肽)发生交叉反应[22],促使减毒活疫苗中的微生物蛋白被抗原提呈细胞上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子以肽片段的形式处理并呈递给T细胞[23],导致有害的自身免疫病。HLA基因的产物与葡萄膜炎的发病相关[23],疫苗肽片段与葡萄膜自身肽之间的氨基酸序列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Garip等[24]认为,机体识别多肽模拟表位并不常见,多肽识别的潜力取决于单个T细胞受体谱系以及相应的HLAⅡ类分子结合和呈递多肽的能力,当遗传易感性个体的HLA基因发生突变时,模拟表位的识别增加,引发强烈的Th1细胞免疫反应(与葡萄膜炎相关的最常见的免疫反应类型[24]),从而增加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的风险。研究表明,无论患者的治疗方案如何,给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接种灭活疫苗是可行的。但对于服用生物药物、改善疾病的抗风湿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的患者由于免疫抑制,建议谨慎接种减毒活疫苗[25]。
临床医生有必要关注VAU作为当前或未来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的危险因素[26]。一些研究报道了免疫接种后患者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部分患者出现过先前疫苗的不良反应[27-29]。此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可出现同时患有两种甚至以上自身免疫病[30]。我们猜测,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来说,在此背景(自身免疫性疾病)下经历分子模拟、免疫复合物沉积和全身免疫反应之后,可能更容易对疫苗产生免疫反应从而发生葡萄膜炎。
部分学者认为乙肝疫苗注射后的VAU除了与疫苗佐剂和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的非特异性免疫激活有关外[31-33],也可能与既往乙肝病毒感染有关[34-35]。既往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乙肝表面抗原可能与接种乙肝疫苗后或者乙肝感染过程中产生的表面抗体相结合为免疫复合物从而导致葡萄膜炎的发生。由此可见,VAU的发生可能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2 各种VAU的流行病学及临床表现
2.1 HBV-VAU
接种HBV疫苗(单独接种或联合接种)后葡萄膜炎报告的平均天数为3 d[36],以视物模糊、头痛、畏光为首发症状来就诊,多表现为视神经炎、视网膜炎等双眼后葡萄膜炎症状,可合并出现关节痛、疲劳、发热等Shoenfeld综合征症状。此外,其发病机制可能还与Ⅲ型超敏反应有关[3]。Fried等[37]认为,免疫复合物的形成及其在外周组织中沉积后激活补体是某些感染和全身性疾病中发生葡萄膜炎的主要机制,接种HBV疫苗后,疫苗的表面抗原可能与接种后免疫应答产生的乙肝抗体形成了免疫复合物,从而引发了葡萄膜炎,在房水中发现抗原抗体复合物可证实[3]。几乎所有接种HBV疫苗后发生的葡萄膜炎均可自愈或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后痊愈。
2.2 HPV-VAU
接种HPV疫苗后发生的葡萄膜炎接种后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30 d[36],主要表现为视神经乳头炎和视网膜炎,也可发生前葡萄膜炎,少数患者可伴有眼压升高从而继发青光眼,严重者可导致失明。据报道,接种HPV疫苗后发生葡萄膜炎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意味着接种HPV疫苗后发生的VAU没有单一的机制[4]。
2.3 流感病毒VAU
接种流感病毒疫苗后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1 d[5]。在接种流感疫苗后1~2 d内,患者可突然出现视力下降伴眼痛,合并前葡萄膜炎KP,虹膜后粘连,前房浮游细胞,可出现房水闪辉伴前房积脓。流感疫苗接种后还可能会出现双侧视神经病变[38]、单纯疱疹性角膜炎[39]、角膜移植排斥反应[39],还有“眼-呼吸综合征”(结膜炎和呼吸道症状)[40]。流感疫苗产生免疫应答引起的小血管炎十分罕见[41],Ⅲ型超敏反应可能是其发病机制。
2.4 卡介苗VAU
接种卡介苗后葡萄膜炎发病病程的中位时间为72 d[5],患者在接种疫苗后多以眼痛、眼红为首发症状,裂隙灯显微镜可见前葡萄膜炎症状,大多发展为全葡萄膜炎,严重者可伴发VKH。葡萄膜炎、浆液性视网膜脱离和VKH综合征可能由分子拟态引起。2016年Dogan等[42]通过比较视网膜蛋白和多肽的氨基酸序列,对卡介苗蛋白序列诱导的强烈Th1反应(与葡萄膜炎相关的最常见的免疫反应类型)进行研究,确定了卡介苗蛋白序列与视网膜自身抗原存在几个高度相似甚至相同的5~11个氨基酸区域。
2.5 MMR-VAU
接种MMR疫苗后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21 d[36],患者以眼痛、眼红为首发症状,裂隙灯显微镜可见典型的前葡萄膜炎体征:前房浮游细胞、房水闪辉、虹膜后粘连、睫状体充血,可伴有前玻璃体腔浮游细胞。在房水中检测到风疹特异性免疫球蛋白(Ig)G抗体可证实MMR联合疫苗引发的VAU,风疹特异性IgG在患眼比对侧眼更明显,在眼内合成并在房水中检测到的抗体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来源:(1)多特异性伴随免疫反应;(2)持久性抗原[43]。MMR联合疫苗是减毒活病毒,其诱发葡萄膜炎可能与视网膜S抗原、感受器间维生素A结合蛋白、脂多糖和脂磷酸有关[5, 44],其潜在机制可能与免疫复合物沉积,随后补体激活的迟发型过敏反应有关[45]。
2.6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VAU
2.7 COVID-19 mRNA-VAU
接种COVID-19疫苗至葡萄膜炎发作之间的平均时间为(7.5±7.3) d[16]。既往文献报告了COVID-19疫苗接种后发生的葡萄膜炎(表1)[48-53]。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预测COVID-19疫苗接种是否会导致疫苗相关葡萄膜炎的发生率高于其他疫苗,但关于BNT162b2 mRNA 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所得出的结果并未强调这种风险增加[54]。患者多以视力下降、眼疼为首发症状,眼科检查可见明显前葡萄膜炎体征,可伴有脉络膜增厚,少数可见视网膜脱离。几乎所有接种疫苗后的VAU患者都在口服或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后痊愈,仅1例严重前葡萄膜炎患者在第2次接种后出现玻璃体炎和黄斑水肿,在玻璃体内注射地塞米松缓释剂后炎症消失[52]。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各国也开始了针对COVID-19各种类型疫苗的研发和紧急接种,眼科医生应关注COVID-19-VAU的可能,给予患者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2.8 联合接种-VAU
3 特殊类型VAU
3.1 MEWDS
既往共报道了4例疫苗后MEWDS。1996年,Baglivo等[57]报道1例乙肝疫苗接种后的MEWDS。2006年,Stangos等[55]报道1例甲型肝炎病毒与黄热病同时接种疫苗后的MEWDS。2014年,Ogino等[58]报道1例HPV疫苗接种后的MEWDS。2018年,Abou-Samra等[59]报道1例接种流感病毒疫苗后的MEWDS。患者多于接种疫苗后2周左右自觉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色觉减退,查体可见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碍,裂隙灯显微镜示前玻璃体浮游细胞,眼底检查示白色斑块,可见黄斑颗粒样改变。FFA显示特征性变化:急性期斑状强荧光或点状强荧光。
3.2 VKH综合征
既往共报道了4例疫苗后VKH病。2016年,Dogan等[42]报道2例卡介苗接种后的VKH综合征,2019年,Sood等[60]报道1例HBV疫苗接种后的VKH综合征。Saraceno等[61]报道1例COVID-19疫苗接种后4 d发生的VKH综合征。患者接种疫苗后3 d左右以头痛、耳鸣、视物模糊、眼痛、畏光为首发症状,眼底可见视盘水肿伴有后极部多灶性鳞状病变。光相干断层扫描示脉络膜增厚、浆液性视网膜脱离。FFA早期示小动脉和小静脉区域的强荧光点显著增加,晚期多湖状荧光积聚。早期脉络膜黑素细胞和巨噬细胞周围由于分子拟态激活的T淋巴细胞聚集异常,导致广泛的脉络膜增厚,是引起VKH综合征的主要病理因素之一[42]。
3.3 APMPPE
1995年Brézin等[62]报道了2例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后APMPPE,患者在接种疫苗后3 d左右,以视力突然下降伴中心暗点为首发症状,眼底可见颞弓内灰白色黄斑病变,长期可导致色素瘢痕形成。FFA示早期弱荧光,晚期强荧光。
4 VAU的治疗和转归
关于VAU的治疗和转归,由于VAU有一定的自限性[5],大多数患者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可自愈,随访观察即可。永久性视力丧失是罕见的[2, 36]。大多数VAU对于糖皮质激素有反应,眼科医生在详细询问疫苗接种史后,对于接种疫苗后的前葡萄膜炎可以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必要时加用散瞳药。对于相对严重的后葡萄膜炎甚至全葡萄膜炎可在局部注射糖皮质激素,必要时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加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和散瞳药,酌情加用相应抗生素进行治疗。如果葡萄膜炎复发,生物疗法(如阿达木单抗)可能被考虑[27]。治疗措施目前仍然缺乏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也尚未达成共识。
5 小结与展望
大规模免疫接种已经对全球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有效消除了多种感染相关的疾病发生率及死亡率,对于人类生存有重要意义。随着疫苗的广泛应用,接种疫苗后发生的眼部不良反应也逐渐被报告。对于临床疑诊VAU的患者,应进行详细的眼科检查。对于临床表现为MEWDS、APMPPE、VKH综合征等特殊类型葡萄膜炎的患者,也应考虑VAU,详细询问其疫苗接种史。对于灭活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接种史患者,应考虑发生Shoenfeld综合征的可能性,仔细寻找其自身免疫性病相关病史、体征及症状,进行自身免疫相关检查,必要时转诊风湿免疫科。但是目前大部分的VAU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是由疫苗诱发的,VAU的发病机制也不明确,治疗措施仍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总而言之,VAU是疫苗接种后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良反应。临床医生在回答患者是否应该接种特定疫苗的询问时,应结合患者自身病史、家族史及体征,充分考虑疫苗接种在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循证医学证据,审慎地给出建议。
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疾病是公共卫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疫苗接种使许多曾经广泛传播、严重或致命传染病的死亡率下降了90%以上[1]。但是,疫苗也可能带来各种副作用,几乎所有种类的疫苗都报道了疫苗相关性葡萄膜炎(VAU)。VAU为接种疫苗后发生的葡萄膜炎,是疫苗接种后一种罕见的不良反应。VAU十分罕见,迄今为止,文献中所报道的各种疫苗引起的VAU大约300例,其发病率为每100 000剂中有8~13剂[2]。VAU最常发生于接种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后(40.5%)[3],其次依次为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15.6%)[4]、流感病毒疫苗(9.7%)、卡介苗疫苗(7.3%)、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MMR)单独或联合疫苗(4.8%)、水痘病毒单独或联合疫苗(4.8%)和甲型肝炎病毒单独或联合疫苗(2.4%)[5]。VAU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平均发病年龄为30岁,从接种疫苗到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16 d[5]。VAU临床多表现为前葡萄膜炎,症状轻微且对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好[5]。但严重者可发生后葡萄膜炎或全葡萄膜炎,如多发性一过性白点综合征(MEWDS)、Vogt-Koyanagi-Harada综合征(VKH)和急性后极部多灶性鳞状色素上皮病变(APMPPE)等[5]。VAU常以视物模糊、眼痛、畏光、眼红为首发症状,可伴有中心暗点、视野缺失、色觉减退,偶见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碍。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结膜充血、角膜后沉着物(KP)、前房浮游细胞、前房闪辉、前玻璃体浮游细胞,严重者可出现前房积脓和虹膜后粘连。眼底检查示视盘水肿伴大量白色病变,偶见黄斑颗粒,长期可形成色素瘢痕。对于不同的并发症,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有不同的表现:当并发APMPPE时可表现为早期弱荧光,晚期强荧光;当并发MEWDS时可表现为早期斑点状强荧光,晚期荧光着染。临床医生需了解VAU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及诊疗建议,避免漏诊及盲目缩小患者疫苗接种适应证。现就VAU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VAU的发病机制
疫苗主要分为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及类毒素疫苗。疫苗的作用原理是注入抗原材料,激活免疫系统对特定病原体产生适应性免疫。但VAU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目前可能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1 疫苗Shoenfeld综合征
Shoenfeld综合征是指由疫苗佐剂(通常为铝盐)引起的自身炎症和免疫反应[6-8]。佐剂包括铝盐、氢氧化物、磷酸盐和硫酸钾。疫苗佐剂能够将免疫反应转变为更多的辅助性T细胞1(Th1)(CD4+)细胞免疫反应[9],从而节省剂量和诱导更快速、更广泛和更强的免疫反应[7-9]。但是,超过耐受机制的自身反应性T细胞可以被外源性佐剂触发成为自身攻击性细胞[10],从而诱发自身免疫或加重自身免疫性疾病。
铝盐是最常见的引发VAU的佐剂,纳米铝颗粒具有独特的跨越血脑屏障和诱导免疫性炎症反应的能力[11-12],在人体内的存续期长且会反复暴露,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和随后的慢性炎症[13]。Shoenfeld综合征常见的全身症状包括关节痛、肌痛和慢性疲劳[7-8],具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佐剂可以诱导免疫系统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随后在遗传易感个体中,自身反应性淋巴细胞的扩张可能会被有缺陷的调节细胞/回路进一步加速[14],继而导致炎症的发生。Shoenfeld综合征最常发生在接种流感病毒疫苗、HPV疫苗、百白破疫苗、MMR疫苗和卡介苗疫苗后[15]。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信使RNA(mRNA)疫苗中包含的佐剂通过包括Toll样受体在内的内溶质或细胞质核酸受体来刺激先天免疫[16],先天免疫系统的激活可导致细胞因子的显著激活,从而诱导葡萄膜炎的发生,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1.2 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的Ⅲ型超敏反应
接种疫苗后,在血液中循环的抗原与免疫应答产生的抗体形成循环免疫复合物,导致血管活性胺如5-羟色胺、组胺和血小板活化因子的释放,增加血管通透性,允许更大的免疫复合物在葡萄膜沉积[6, 17]。免疫复合物沉积后激活补体系统,导致白细胞趋化和组织肥大细胞脱颗粒[18],引起Ⅲ型超敏反应[3],组织损伤加重,引发葡萄膜炎。但是由于循环免疫复合物的特性和血房水屏障的存在,只有少数循环免疫复合物沉积的现象会导致VAU的发生,当合并有全身性免疫复合体疾病并伴有巩膜和角膜缘血液回流障碍时,由于这些无血管结构的营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管层,因此,免疫神经丛可能在角膜周围和巩膜坏死和溃疡等危险情况下发挥作用[18],导致接种疫苗后葡萄膜炎发生的概率增加。该机制下发生的VAU,大多能在房水中检测到循环免疫复合物[3]。研究报道,迟发型超敏反应也可能是VAU的发病机制之一[19]。
1.3 减毒活疫苗的直接感染
一部分VAU是由减毒活疫苗的活株诱导眼结构的直接感染所致[19]。Guex-Crosier等[20]假设卡介苗接种后眼部炎症的可能是由于分枝杆菌的直接感染。与这一理论相一致的是,Llorenç等[21]在体外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细胞模型中发现,卡介苗能够感染RPE细胞,并在细胞内复制直到细胞溶解,活化的RPE细胞具有巨噬细胞样的功能,可形成非干酪性肉芽肿。抗生素治疗的相对有效性是证实这一假设的另一个线索[5,19]。此外,卡介苗感染细胞48 h后细胞增生明显增强,卡介苗的这种促增生作用可以解释临床上观察到的部分患者的RPE增生[21]。另外,在带状疱疹疫苗不良反应报告中,也存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皮肤疱疹液及玻璃体液证实接种后特定病毒的持续复制[19]。
1.4 分子拟态理论及VAU与自身免疫病的关系
疫苗肽片段和葡萄膜自身肽之间的分子具有相似性。在接种疫苗后,机体针对减毒株产生的免疫反应可以与减毒株共享肽序列(或结构)的人类蛋白质(葡萄膜自身肽)发生交叉反应[22],促使减毒活疫苗中的微生物蛋白被抗原提呈细胞上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子以肽片段的形式处理并呈递给T细胞[23],导致有害的自身免疫病。HLA基因的产物与葡萄膜炎的发病相关[23],疫苗肽片段与葡萄膜自身肽之间的氨基酸序列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Garip等[24]认为,机体识别多肽模拟表位并不常见,多肽识别的潜力取决于单个T细胞受体谱系以及相应的HLAⅡ类分子结合和呈递多肽的能力,当遗传易感性个体的HLA基因发生突变时,模拟表位的识别增加,引发强烈的Th1细胞免疫反应(与葡萄膜炎相关的最常见的免疫反应类型[24]),从而增加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的风险。研究表明,无论患者的治疗方案如何,给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接种灭活疫苗是可行的。但对于服用生物药物、改善疾病的抗风湿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的患者由于免疫抑制,建议谨慎接种减毒活疫苗[25]。
临床医生有必要关注VAU作为当前或未来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的危险因素[26]。一些研究报道了免疫接种后患者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部分患者出现过先前疫苗的不良反应[27-29]。此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可出现同时患有两种甚至以上自身免疫病[30]。我们猜测,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来说,在此背景(自身免疫性疾病)下经历分子模拟、免疫复合物沉积和全身免疫反应之后,可能更容易对疫苗产生免疫反应从而发生葡萄膜炎。
部分学者认为乙肝疫苗注射后的VAU除了与疫苗佐剂和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的非特异性免疫激活有关外[31-33],也可能与既往乙肝病毒感染有关[34-35]。既往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乙肝表面抗原可能与接种乙肝疫苗后或者乙肝感染过程中产生的表面抗体相结合为免疫复合物从而导致葡萄膜炎的发生。由此可见,VAU的发生可能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2 各种VAU的流行病学及临床表现
2.1 HBV-VAU
接种HBV疫苗(单独接种或联合接种)后葡萄膜炎报告的平均天数为3 d[36],以视物模糊、头痛、畏光为首发症状来就诊,多表现为视神经炎、视网膜炎等双眼后葡萄膜炎症状,可合并出现关节痛、疲劳、发热等Shoenfeld综合征症状。此外,其发病机制可能还与Ⅲ型超敏反应有关[3]。Fried等[37]认为,免疫复合物的形成及其在外周组织中沉积后激活补体是某些感染和全身性疾病中发生葡萄膜炎的主要机制,接种HBV疫苗后,疫苗的表面抗原可能与接种后免疫应答产生的乙肝抗体形成了免疫复合物,从而引发了葡萄膜炎,在房水中发现抗原抗体复合物可证实[3]。几乎所有接种HBV疫苗后发生的葡萄膜炎均可自愈或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后痊愈。
2.2 HPV-VAU
接种HPV疫苗后发生的葡萄膜炎接种后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30 d[36],主要表现为视神经乳头炎和视网膜炎,也可发生前葡萄膜炎,少数患者可伴有眼压升高从而继发青光眼,严重者可导致失明。据报道,接种HPV疫苗后发生葡萄膜炎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意味着接种HPV疫苗后发生的VAU没有单一的机制[4]。
2.3 流感病毒VAU
接种流感病毒疫苗后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1 d[5]。在接种流感疫苗后1~2 d内,患者可突然出现视力下降伴眼痛,合并前葡萄膜炎KP,虹膜后粘连,前房浮游细胞,可出现房水闪辉伴前房积脓。流感疫苗接种后还可能会出现双侧视神经病变[38]、单纯疱疹性角膜炎[39]、角膜移植排斥反应[39],还有“眼-呼吸综合征”(结膜炎和呼吸道症状)[40]。流感疫苗产生免疫应答引起的小血管炎十分罕见[41],Ⅲ型超敏反应可能是其发病机制。
2.4 卡介苗VAU
接种卡介苗后葡萄膜炎发病病程的中位时间为72 d[5],患者在接种疫苗后多以眼痛、眼红为首发症状,裂隙灯显微镜可见前葡萄膜炎症状,大多发展为全葡萄膜炎,严重者可伴发VKH。葡萄膜炎、浆液性视网膜脱离和VKH综合征可能由分子拟态引起。2016年Dogan等[42]通过比较视网膜蛋白和多肽的氨基酸序列,对卡介苗蛋白序列诱导的强烈Th1反应(与葡萄膜炎相关的最常见的免疫反应类型)进行研究,确定了卡介苗蛋白序列与视网膜自身抗原存在几个高度相似甚至相同的5~11个氨基酸区域。
2.5 MMR-VAU
接种MMR疫苗后葡萄膜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21 d[36],患者以眼痛、眼红为首发症状,裂隙灯显微镜可见典型的前葡萄膜炎体征:前房浮游细胞、房水闪辉、虹膜后粘连、睫状体充血,可伴有前玻璃体腔浮游细胞。在房水中检测到风疹特异性免疫球蛋白(Ig)G抗体可证实MMR联合疫苗引发的VAU,风疹特异性IgG在患眼比对侧眼更明显,在眼内合成并在房水中检测到的抗体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来源:(1)多特异性伴随免疫反应;(2)持久性抗原[43]。MMR联合疫苗是减毒活病毒,其诱发葡萄膜炎可能与视网膜S抗原、感受器间维生素A结合蛋白、脂多糖和脂磷酸有关[5, 44],其潜在机制可能与免疫复合物沉积,随后补体激活的迟发型过敏反应有关[45]。
2.6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VAU
2.7 COVID-19 mRNA-VAU
接种COVID-19疫苗至葡萄膜炎发作之间的平均时间为(7.5±7.3) d[16]。既往文献报告了COVID-19疫苗接种后发生的葡萄膜炎(表1)[48-53]。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预测COVID-19疫苗接种是否会导致疫苗相关葡萄膜炎的发生率高于其他疫苗,但关于BNT162b2 mRNA 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所得出的结果并未强调这种风险增加[54]。患者多以视力下降、眼疼为首发症状,眼科检查可见明显前葡萄膜炎体征,可伴有脉络膜增厚,少数可见视网膜脱离。几乎所有接种疫苗后的VAU患者都在口服或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后痊愈,仅1例严重前葡萄膜炎患者在第2次接种后出现玻璃体炎和黄斑水肿,在玻璃体内注射地塞米松缓释剂后炎症消失[52]。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各国也开始了针对COVID-19各种类型疫苗的研发和紧急接种,眼科医生应关注COVID-19-VAU的可能,给予患者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2.8 联合接种-VAU
3 特殊类型VAU
3.1 MEWDS
既往共报道了4例疫苗后MEWDS。1996年,Baglivo等[57]报道1例乙肝疫苗接种后的MEWDS。2006年,Stangos等[55]报道1例甲型肝炎病毒与黄热病同时接种疫苗后的MEWDS。2014年,Ogino等[58]报道1例HPV疫苗接种后的MEWDS。2018年,Abou-Samra等[59]报道1例接种流感病毒疫苗后的MEWDS。患者多于接种疫苗后2周左右自觉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色觉减退,查体可见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碍,裂隙灯显微镜示前玻璃体浮游细胞,眼底检查示白色斑块,可见黄斑颗粒样改变。FFA显示特征性变化:急性期斑状强荧光或点状强荧光。
3.2 VKH综合征
既往共报道了4例疫苗后VKH病。2016年,Dogan等[42]报道2例卡介苗接种后的VKH综合征,2019年,Sood等[60]报道1例HBV疫苗接种后的VKH综合征。Saraceno等[61]报道1例COVID-19疫苗接种后4 d发生的VKH综合征。患者接种疫苗后3 d左右以头痛、耳鸣、视物模糊、眼痛、畏光为首发症状,眼底可见视盘水肿伴有后极部多灶性鳞状病变。光相干断层扫描示脉络膜增厚、浆液性视网膜脱离。FFA早期示小动脉和小静脉区域的强荧光点显著增加,晚期多湖状荧光积聚。早期脉络膜黑素细胞和巨噬细胞周围由于分子拟态激活的T淋巴细胞聚集异常,导致广泛的脉络膜增厚,是引起VKH综合征的主要病理因素之一[42]。
3.3 APMPPE
1995年Brézin等[62]报道了2例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后APMPPE,患者在接种疫苗后3 d左右,以视力突然下降伴中心暗点为首发症状,眼底可见颞弓内灰白色黄斑病变,长期可导致色素瘢痕形成。FFA示早期弱荧光,晚期强荧光。
4 VAU的治疗和转归
关于VAU的治疗和转归,由于VAU有一定的自限性[5],大多数患者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可自愈,随访观察即可。永久性视力丧失是罕见的[2, 36]。大多数VAU对于糖皮质激素有反应,眼科医生在详细询问疫苗接种史后,对于接种疫苗后的前葡萄膜炎可以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必要时加用散瞳药。对于相对严重的后葡萄膜炎甚至全葡萄膜炎可在局部注射糖皮质激素,必要时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加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和散瞳药,酌情加用相应抗生素进行治疗。如果葡萄膜炎复发,生物疗法(如阿达木单抗)可能被考虑[27]。治疗措施目前仍然缺乏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也尚未达成共识。
5 小结与展望
大规模免疫接种已经对全球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有效消除了多种感染相关的疾病发生率及死亡率,对于人类生存有重要意义。随着疫苗的广泛应用,接种疫苗后发生的眼部不良反应也逐渐被报告。对于临床疑诊VAU的患者,应进行详细的眼科检查。对于临床表现为MEWDS、APMPPE、VKH综合征等特殊类型葡萄膜炎的患者,也应考虑VAU,详细询问其疫苗接种史。对于灭活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接种史患者,应考虑发生Shoenfeld综合征的可能性,仔细寻找其自身免疫性病相关病史、体征及症状,进行自身免疫相关检查,必要时转诊风湿免疫科。但是目前大部分的VAU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是由疫苗诱发的,VAU的发病机制也不明确,治疗措施仍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总而言之,VAU是疫苗接种后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良反应。临床医生在回答患者是否应该接种特定疫苗的询问时,应结合患者自身病史、家族史及体征,充分考虑疫苗接种在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循证医学证据,审慎地给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