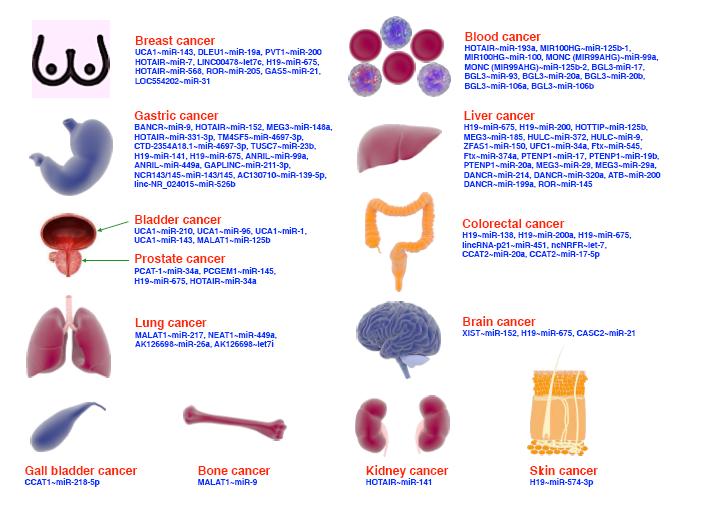葡萄膜黑色素瘤(UM)是眼内侵袭性强且致命的肿瘤。由于UM及其微环境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导致缺乏早期预防和治疗转移的策略。单细胞测序技术通过在单个细胞层面进行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表观遗传学的分析,为破译肿瘤内异质性和微环境的复杂性提供了关键的视角。通过生物信息分析,并结合人工智能算法,有助于寻找预后相关的分子指标和治疗靶点,为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但单细胞测序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样本要求高、测序花费昂贵和耗时长等。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完善和分析方法的更新,这些缺点可被逐步解决,未来终将攻克这一罕见肿瘤,实现UM患者长期生存的目标。
引用本文: 赵汉卿, 罗婧婷, 李洋, 魏文斌. 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在葡萄膜黑色素瘤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2, 38(3): 248-252.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20130-00063 复制
版权信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期刊社《中华眼底病杂志》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改编
葡萄膜黑色素瘤(UM)是成年人眼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主要来源于脉络膜黑素细胞(90%),部分来自睫状体的黑素细胞(6%)或虹膜的黑素细胞(4%)[1]。UM是一种罕见的肿瘤,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和地区差异,发病率约0.3%~8.0%,其中亚洲的发病率显著低于欧美[2]。由于缺乏精准的分子靶点,UM的治疗方式以手术和敷贴放射治疗为主。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疗效常不理想,呈低反应率甚至无反应率[3]。UM的侵袭性极强,约50%的患者在治疗后发生转移[4]。然而对于这种转移尚无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发展为突破这一困境带来了希望。其通过从单个细胞中获取转录组信息,挖掘同一肿瘤内癌细胞基因表达的差异性,揭示肿瘤微环境(TME)的细胞组成,有利于获取罕见肿瘤的生物学信息。一些基于单细胞测序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结合生物信息学和人工智能算法,有助于构建UM发生、发展、复发、转移和预后相关的分子指标体系,寻找治疗靶点,为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现就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在UM中的应用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单细胞测序的技术特点
单细胞测序是指在单个细胞水平上对转录组或基因组进行扩增并测序,以检测单细胞在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学和蛋白组学等生物信息的技术。首先从新鲜组织分离单细胞,进行细胞溶解、获取核酸和扩增,最后进行测序和分析[5]。这种技术能够探索复杂组织中单个细胞的不同生物学特性,了解细胞亚群对不同微环境的反应,有助于研究细胞分化、增生和肿瘤发生等过程。
传统测序分析在探究UM的肿瘤特征、分子机制和微环境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最具代表性的是2017年Robertson等[6]的研究,他们对80个原发性UM患者的肿瘤组织进行全面多平台分析,采用一系列测序技术(包括DNA-seq和RNA-seq),获取了UM的DNA、mRNA、非编码RNA表达数据,DNA甲基化、突变和拷贝数的数据综合分析,最终鉴定并表征了4种不同预后的亚型,即A期:3号染色体二倍体、8q拷贝数正常;B期:3号染色体二倍体,8q拷贝数扩增;C期:单体3、8q拷贝数扩增;D期:单体3、8q拷贝数多倍扩增。从A期到D期患者预后愈差,转移风险愈高。这80个UM组织的测序信息在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CGA)中公开(https://portal.gdc.cancer.gov/),供研究者下载使用。随后大量的研究基于TCGA数据库,探索了UM中的生物学特点,如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肿瘤的纯度、免疫浸润特点和免疫相关基因等[7-8]。传统测序针对的是组织中的所有细胞,获取全部信息,但只能反映所有细胞的平均变异水平,无法揭示单个细胞的遗传信息。而且可能遗漏少数的细胞亚型。单细胞测序的出现为破译这一难题带来了曙光,能以最小的样本量,展开高分辨率的分析。从单细胞的角度出发,探测细胞特异性、差异性和细胞间的协同运作方式,揭示每个细胞独特的遗传信息,并发现新的细胞类型。
目前大规模运用的单细胞测序平台有Illumina、BD Rhapsody、10x Chromium、ICELL8 和C1™单细胞全自动制备系统。应用广泛的单细胞测序技术包括单细胞基因组测序、scRNA-seq和表观遗传测序。scRNA-seq通过提取RNA,将捕获的信使RNA反转录为cDNA,再进行全转录组的测序分析。其可以直观地反应基因表达情况,解释细胞种类、亚型、状态和发展轨迹[9]。
2 scRNA-seq分析在UM中的应用
2.1 揭示肿瘤的异质性
肿瘤异质性是指肿瘤在生长过程中,经过多次分裂增生,子细胞在分子生物学或基因层面的改变,从而导致生长速度、侵袭能力、药敏性和预后等各方面产生差异[10]。异质性不仅存在于肿瘤之间,也存在于一个肿瘤内。
2020年Durante等[11]的研究为scRNA-seq分析揭示UM生物学特征拉开了序幕。这项重要的研究分别对8个原发性UM肿瘤和3个转移性UM肿瘤,共计59 915个细胞行scRNA-seq分析,揭露了肿瘤和免疫细胞复杂的生态环境。对细胞亚群进行分类发现,从原位肿瘤到转移肿瘤,细胞类型的复杂度增加。其中基因表达谱(GEP)分型为2类的原发肿瘤和转移肿瘤中含有丰富的浸润性免疫细胞,通过剖析这类肿瘤寻找线索,可为开发免疫疗法提供重要信息。然而这项研究并未深入分析原发性和转移性UM之间的细胞类型和分子表达的差异。
2021年Pandiani等[12]对6个原发性UM肿瘤,共计7 890个单细胞行scRNA-seq并进行多尺度分析,揭示了肿瘤内异质性,深入研究了UM转移过程中的调节机制,推断出3种转录状态的特征:(1)与细胞特异性有关,包括基因SOX9、SOX10和PAX3;(2)与免疫反应和炎症有关,包括基因BCL3、CEBPB和AP1成员(JUNB、JUND、FOS和FOSB);(3)与肿瘤的侵袭性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被归类为与预后良好患者的肿瘤中,也可检测到预后不良的肿瘤细胞。
两项研究均通过推断染色体拷贝数变异,强调基因组异质性,发现了一些传统测序未检测到的基因组改变[12-13]。而Bertolotto[13]认为,染色体拷贝数变异识别的隐匿性改变可能由拓扑相关结构域或染色质纳米结构域水平上的转录调控引起。
2.1.1 探索复杂的TME
肿瘤组织并非只有肿瘤细胞,还包括免疫和炎症细胞、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及细胞因子等统称为TME[14]。浸润到肿瘤内部的淋巴细胞介导了免疫相关的TME,表现出免疫抑制,有利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和免疫逃逸。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基质细胞构成肿瘤非免疫微环境。肿瘤细胞和TME两者相辅相成,TME在肿瘤的发展、免疫反应和治疗疗效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与皮肤黑色素瘤相比,UM具有较低的肿瘤突变负担和促瘤的免疫微环境[15]。眼睛作为免疫特权部位,抑制免疫,限制淋巴循环,最终导致CD8+ T细胞的耗竭。UM免疫微环境含有大量的M2型巨噬细胞和CD8+ T细胞[16],其中CD8+ T细胞代表UM患者的不良预后[15]。在单体3肿瘤中,含有更多的M2型巨噬细胞浸润[17],染色体8q的扩增可能和巨噬细胞增多有关[18],大量T细胞浸润与BAP1基因缺失有关[19]。
Pandiani等[12]研究发现,原发性UM仅有少量的免疫浸润,这符合主流的观点。而Durante等[11]研究却发现,有少数UM患者存在大量免疫浸润,且GEP分型为2类肿瘤者免疫浸润水平更高,与Robertson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Durante等[11]还发现,淋巴细胞活化蛋白(LAG3)T细胞的抑制性免疫检查点才是UM中的主要衰竭指标,而非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LAT-4)。这可部分解释抗PD-1和抗CTLA-4治疗失败的事实。实际上,Triozzi等[18]在2014年就已发现UM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含有高表达的LAG3。现有大量临床试验评估LAG-3抑制剂在多种癌症中的治疗效果,其中有一项临床研究(NCT02519322)应用relatlimab(LAG-3抑制剂)治疗晚期UM[13]。
总之,两项研究都在单细胞水平上探索,但侧重方向不同。Durante等[11]的研究关注TME和免疫浸润环境;而Pandiani等[12]的研究关注基因组和转录组层面肿瘤的异质性,以及不同转录状态的特征。两项研究互为验证,相互补充,有助于全面地理解UM的转移和免疫浸润。
2.1.2 探索UM肝转移瘤的异质性
2021年Lin等[20]利用scRNA-seq和拷贝数改变分析1例UM患者2个并发的肝转移灶,发现肝转移瘤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一个转移灶由梭形细胞和上皮样细胞组成,另一个转移灶只含上皮样细胞。含有梭形细胞的转移灶能观察到染色体9p缺失和染色体8q扩增,这与2019年Shain等[21]提出的转移性UM的特征一致。仅含上皮样细胞的肝转移灶中T细胞高表达LAG3基因,这种转移灶之间差异性可能会指导不同的治疗决策。
Pandiani等[12]的研究证明了HES6基因能够增强肿瘤生长和侵袭能力,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虽然Lin等[20]也证实HES6基因在两个肝转移灶中表达增加,含梭形细胞的肝转移灶中HES6基因的表达较低,说明UM并非完全依赖HES6基因信号,还有其他信号可驱动肿瘤转移。这项研究证实了UM肝转移灶的复杂性,扩宽了UM单细胞层面的转录组图谱,强调了准确评估肿瘤特点,及时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决策的重要性。
2.2 揭示新的发病机制
2021年,Bakhoum等[22]通过整合单细胞水平上的信息,探索染色体不稳定性和表观遗传学与肿瘤进展和转移的关系,揭示了UM进展的关键步骤,即由Polycomb抑制复合物1(PRC1)缺失驱动一系列分子的改变,从而将表观遗传学、组织学和转录特征联系起来。Polycomb蛋白家族是一类通过表观遗传修饰调控靶基因的转录因子。主要功能是对转录调节的作用,通过抑制靶基因转录使靶基因沉默。此外,Polycomb蛋白家族构成高级染色质结构,因此它们的缺失可使基因组拓扑结构的错构导致染色体不稳定。PRC1的缺失导致靶基因转录去抑制,使染色体分离错误,促进利于转移的慢性炎症信号。此外,PRC1的缺失使核增大并向上皮样形态转变,通常认为上皮样细胞型UM比梭形细胞型UM的预后更差[23]。
这项研究反对独立克隆起源的观点,对UM进展的分子机制提出了新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最初预后良好的UM可能获得恶性的表型。未来还需要探索PRC1缺失的下游通路,寻找治疗的潜在靶点。
2.3 完善预后预测的工具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八版[24]根据肿瘤的大小(直径和厚度)、解剖范围(睫状体受累和巩膜外延伸)对UM分类。随着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发现3号染色体的缺失和8号染色体的增加与预后差相关[25]。因此Dogrusöz等[26]和Bagger等[27]将染色体信息加入AJCC分期系统进一步完善预后的预测。2004年,Onken等[28]采用原发性UM转录组分析中的无监督聚类揭示了基于GEP的两个分类,预后较好的1类和预后较差的2类。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应用,补充了驱动基因层面的研究,鉴定了UM的初级驱动基因(GNAQ、GNA11)和次级驱动基因(BAP1、SF3B1、EIF1MX)。约90%的UM存在GNAQ、GNA11基因突变,激活肿瘤的发生。BAP1基因突变临床预后最差,SF3B1次之,EIF1MX最佳[29]。
Pandiani等[12]对6个原发性UM肿瘤行scRNA-seq分析,针对1 000个最多变基因行主成分分析,将细胞和基因按照主成分(PC)分数排序,构建了基于PC值的预后预测模型。采用TCGA数据库进行Kaplan-Meier验证,PC值高的基因与总体存活率低相关。其中,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成分β2-微球蛋白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A都是PC值高的基因,而在UM中HLA Ⅰ类或HLA Ⅱ类抗原的高表达预示预后差[30]。
Strub等[13]评价了4种预后模型对生存率的预测能力,包括单体3、基于基因表达和DNA 甲基化谱提取出的11个预后相关基因签名[31]、GEP分型[28]、单细胞分析构建的PC1模型。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每种预后分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它们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79、077、0.85、0.85,证实了基于PC值的签名预测预后更加准确。
Liu等[32]使用GSE139839数据集(Durante的单细胞测序数据)探索与UM免疫环境相关的m6A调节因子和长链非编码RNA,开发基于m6A的基因签名有助于提高对患者的预后预测。
CD8+ T细胞被认为是UM不良预后的指标[33]。Sun等[34]探索了CD8+ T细胞在UM中预测预后和对免疫治疗反应的作用。通过结合GSE139839数据集(Durante的单细胞测序数据),筛选出与CD8+ T细胞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采用多种机器学习的算法构建了CD8+ T细胞相关的基因签名,包括3个与肿瘤或免疫反应相关基因IFNGR1、ANXA6和TANK。这种基因签名可促进免疫监测,拯救耗尽的CD8+ T细胞,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疗效。
综上所述,在单细胞水平上,从RNA甲基化、免疫等不同角度挖掘预后的生物学特征,结合人工智能方法,可以辅助完善预后相关的分子指标体系。
2.4 scRNA-seq有助于寻找治疗靶点
Gαq信号通路的激活是UM进展中常见的早期事件,主要特点是GNAQ或GNA11基因突变,还包括较罕见的基因CYSLTR2[35]。基因CYSLTR2编码G蛋白偶联受体半胱氨酸白三烯受体2(CysLT2R),该受体参与白三烯介导的信号传导[36]。CYSLTR2基因突变导致内源性Gαq信号激活,从而刺激与GNAQ和GNA11中致癌突变相同的途径[37]。
Nell等[38]用数字型聚合酶链反应结合公共数据库分析发现,CYSLTR2基因参与UM的早期和晚期进展。其中,CYSLTR2p.L129Q突变可能是起始致癌事件。随着肿瘤进展,CYSLTR2突变等位基因的表达丰度不断增加,结果说明突变型CysLT2R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Pandiani等[12]发现转录因子HES6在UM中具有驱动肿瘤的侵袭性和不良预后等重要作用;该研究运用鸡胚绒毛尿囊膜试验证实,HES6的缺失会在体外和体内抑制肿瘤增生、迁移和转移播散。这提示,HES6及其靶基因可能作为治疗的靶点。
3 不足与展望
单细胞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样本要求高、测序花费昂贵和耗时长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完善和分析方法的更新,这些缺点可被逐步解决。目前公开的仅有17个UM样本的单细胞测序数据,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具有局限性,不适用于所有患者。此外,除了已经阐明的研究问题,还可对公开的单细胞数据挖掘,更加细致的研究肿瘤的起源、进展和免疫浸润。最终,将研究结果回归临床,开发出有效的诊断、预后分级和治疗肿瘤转移的方法,才能最大地发挥单细胞测序的优势。
UM是成人眼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因其易转移、对化学治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均不敏感的特点,使得转移的早期诊断、治疗和干预都十分困难。肿瘤的异质性增加了探索UM生物学特征的复杂性。对UM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挑战,许多问题至今还在探索中,例如如何识别肿瘤转移早期,如何有效治疗肿瘤转移且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等。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发展为研究者和患者带来了希望,随着技术的更新和不断完善,未来终将攻克这一罕见肿瘤,实现UM患者长期生存的目标。
葡萄膜黑色素瘤(UM)是成年人眼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主要来源于脉络膜黑素细胞(90%),部分来自睫状体的黑素细胞(6%)或虹膜的黑素细胞(4%)[1]。UM是一种罕见的肿瘤,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和地区差异,发病率约0.3%~8.0%,其中亚洲的发病率显著低于欧美[2]。由于缺乏精准的分子靶点,UM的治疗方式以手术和敷贴放射治疗为主。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疗效常不理想,呈低反应率甚至无反应率[3]。UM的侵袭性极强,约50%的患者在治疗后发生转移[4]。然而对于这种转移尚无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发展为突破这一困境带来了希望。其通过从单个细胞中获取转录组信息,挖掘同一肿瘤内癌细胞基因表达的差异性,揭示肿瘤微环境(TME)的细胞组成,有利于获取罕见肿瘤的生物学信息。一些基于单细胞测序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结合生物信息学和人工智能算法,有助于构建UM发生、发展、复发、转移和预后相关的分子指标体系,寻找治疗靶点,为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现就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在UM中的应用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单细胞测序的技术特点
单细胞测序是指在单个细胞水平上对转录组或基因组进行扩增并测序,以检测单细胞在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学和蛋白组学等生物信息的技术。首先从新鲜组织分离单细胞,进行细胞溶解、获取核酸和扩增,最后进行测序和分析[5]。这种技术能够探索复杂组织中单个细胞的不同生物学特性,了解细胞亚群对不同微环境的反应,有助于研究细胞分化、增生和肿瘤发生等过程。
传统测序分析在探究UM的肿瘤特征、分子机制和微环境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最具代表性的是2017年Robertson等[6]的研究,他们对80个原发性UM患者的肿瘤组织进行全面多平台分析,采用一系列测序技术(包括DNA-seq和RNA-seq),获取了UM的DNA、mRNA、非编码RNA表达数据,DNA甲基化、突变和拷贝数的数据综合分析,最终鉴定并表征了4种不同预后的亚型,即A期:3号染色体二倍体、8q拷贝数正常;B期:3号染色体二倍体,8q拷贝数扩增;C期:单体3、8q拷贝数扩增;D期:单体3、8q拷贝数多倍扩增。从A期到D期患者预后愈差,转移风险愈高。这80个UM组织的测序信息在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CGA)中公开(https://portal.gdc.cancer.gov/),供研究者下载使用。随后大量的研究基于TCGA数据库,探索了UM中的生物学特点,如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肿瘤的纯度、免疫浸润特点和免疫相关基因等[7-8]。传统测序针对的是组织中的所有细胞,获取全部信息,但只能反映所有细胞的平均变异水平,无法揭示单个细胞的遗传信息。而且可能遗漏少数的细胞亚型。单细胞测序的出现为破译这一难题带来了曙光,能以最小的样本量,展开高分辨率的分析。从单细胞的角度出发,探测细胞特异性、差异性和细胞间的协同运作方式,揭示每个细胞独特的遗传信息,并发现新的细胞类型。
目前大规模运用的单细胞测序平台有Illumina、BD Rhapsody、10x Chromium、ICELL8 和C1™单细胞全自动制备系统。应用广泛的单细胞测序技术包括单细胞基因组测序、scRNA-seq和表观遗传测序。scRNA-seq通过提取RNA,将捕获的信使RNA反转录为cDNA,再进行全转录组的测序分析。其可以直观地反应基因表达情况,解释细胞种类、亚型、状态和发展轨迹[9]。
2 scRNA-seq分析在UM中的应用
2.1 揭示肿瘤的异质性
肿瘤异质性是指肿瘤在生长过程中,经过多次分裂增生,子细胞在分子生物学或基因层面的改变,从而导致生长速度、侵袭能力、药敏性和预后等各方面产生差异[10]。异质性不仅存在于肿瘤之间,也存在于一个肿瘤内。
2020年Durante等[11]的研究为scRNA-seq分析揭示UM生物学特征拉开了序幕。这项重要的研究分别对8个原发性UM肿瘤和3个转移性UM肿瘤,共计59 915个细胞行scRNA-seq分析,揭露了肿瘤和免疫细胞复杂的生态环境。对细胞亚群进行分类发现,从原位肿瘤到转移肿瘤,细胞类型的复杂度增加。其中基因表达谱(GEP)分型为2类的原发肿瘤和转移肿瘤中含有丰富的浸润性免疫细胞,通过剖析这类肿瘤寻找线索,可为开发免疫疗法提供重要信息。然而这项研究并未深入分析原发性和转移性UM之间的细胞类型和分子表达的差异。
2021年Pandiani等[12]对6个原发性UM肿瘤,共计7 890个单细胞行scRNA-seq并进行多尺度分析,揭示了肿瘤内异质性,深入研究了UM转移过程中的调节机制,推断出3种转录状态的特征:(1)与细胞特异性有关,包括基因SOX9、SOX10和PAX3;(2)与免疫反应和炎症有关,包括基因BCL3、CEBPB和AP1成员(JUNB、JUND、FOS和FOSB);(3)与肿瘤的侵袭性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被归类为与预后良好患者的肿瘤中,也可检测到预后不良的肿瘤细胞。
两项研究均通过推断染色体拷贝数变异,强调基因组异质性,发现了一些传统测序未检测到的基因组改变[12-13]。而Bertolotto[13]认为,染色体拷贝数变异识别的隐匿性改变可能由拓扑相关结构域或染色质纳米结构域水平上的转录调控引起。
2.1.1 探索复杂的TME
肿瘤组织并非只有肿瘤细胞,还包括免疫和炎症细胞、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及细胞因子等统称为TME[14]。浸润到肿瘤内部的淋巴细胞介导了免疫相关的TME,表现出免疫抑制,有利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和免疫逃逸。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基质细胞构成肿瘤非免疫微环境。肿瘤细胞和TME两者相辅相成,TME在肿瘤的发展、免疫反应和治疗疗效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与皮肤黑色素瘤相比,UM具有较低的肿瘤突变负担和促瘤的免疫微环境[15]。眼睛作为免疫特权部位,抑制免疫,限制淋巴循环,最终导致CD8+ T细胞的耗竭。UM免疫微环境含有大量的M2型巨噬细胞和CD8+ T细胞[16],其中CD8+ T细胞代表UM患者的不良预后[15]。在单体3肿瘤中,含有更多的M2型巨噬细胞浸润[17],染色体8q的扩增可能和巨噬细胞增多有关[18],大量T细胞浸润与BAP1基因缺失有关[19]。
Pandiani等[12]研究发现,原发性UM仅有少量的免疫浸润,这符合主流的观点。而Durante等[11]研究却发现,有少数UM患者存在大量免疫浸润,且GEP分型为2类肿瘤者免疫浸润水平更高,与Robertson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Durante等[11]还发现,淋巴细胞活化蛋白(LAG3)T细胞的抑制性免疫检查点才是UM中的主要衰竭指标,而非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LAT-4)。这可部分解释抗PD-1和抗CTLA-4治疗失败的事实。实际上,Triozzi等[18]在2014年就已发现UM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含有高表达的LAG3。现有大量临床试验评估LAG-3抑制剂在多种癌症中的治疗效果,其中有一项临床研究(NCT02519322)应用relatlimab(LAG-3抑制剂)治疗晚期UM[13]。
总之,两项研究都在单细胞水平上探索,但侧重方向不同。Durante等[11]的研究关注TME和免疫浸润环境;而Pandiani等[12]的研究关注基因组和转录组层面肿瘤的异质性,以及不同转录状态的特征。两项研究互为验证,相互补充,有助于全面地理解UM的转移和免疫浸润。
2.1.2 探索UM肝转移瘤的异质性
2021年Lin等[20]利用scRNA-seq和拷贝数改变分析1例UM患者2个并发的肝转移灶,发现肝转移瘤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一个转移灶由梭形细胞和上皮样细胞组成,另一个转移灶只含上皮样细胞。含有梭形细胞的转移灶能观察到染色体9p缺失和染色体8q扩增,这与2019年Shain等[21]提出的转移性UM的特征一致。仅含上皮样细胞的肝转移灶中T细胞高表达LAG3基因,这种转移灶之间差异性可能会指导不同的治疗决策。
Pandiani等[12]的研究证明了HES6基因能够增强肿瘤生长和侵袭能力,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虽然Lin等[20]也证实HES6基因在两个肝转移灶中表达增加,含梭形细胞的肝转移灶中HES6基因的表达较低,说明UM并非完全依赖HES6基因信号,还有其他信号可驱动肿瘤转移。这项研究证实了UM肝转移灶的复杂性,扩宽了UM单细胞层面的转录组图谱,强调了准确评估肿瘤特点,及时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决策的重要性。
2.2 揭示新的发病机制
2021年,Bakhoum等[22]通过整合单细胞水平上的信息,探索染色体不稳定性和表观遗传学与肿瘤进展和转移的关系,揭示了UM进展的关键步骤,即由Polycomb抑制复合物1(PRC1)缺失驱动一系列分子的改变,从而将表观遗传学、组织学和转录特征联系起来。Polycomb蛋白家族是一类通过表观遗传修饰调控靶基因的转录因子。主要功能是对转录调节的作用,通过抑制靶基因转录使靶基因沉默。此外,Polycomb蛋白家族构成高级染色质结构,因此它们的缺失可使基因组拓扑结构的错构导致染色体不稳定。PRC1的缺失导致靶基因转录去抑制,使染色体分离错误,促进利于转移的慢性炎症信号。此外,PRC1的缺失使核增大并向上皮样形态转变,通常认为上皮样细胞型UM比梭形细胞型UM的预后更差[23]。
这项研究反对独立克隆起源的观点,对UM进展的分子机制提出了新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最初预后良好的UM可能获得恶性的表型。未来还需要探索PRC1缺失的下游通路,寻找治疗的潜在靶点。
2.3 完善预后预测的工具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八版[24]根据肿瘤的大小(直径和厚度)、解剖范围(睫状体受累和巩膜外延伸)对UM分类。随着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发现3号染色体的缺失和8号染色体的增加与预后差相关[25]。因此Dogrusöz等[26]和Bagger等[27]将染色体信息加入AJCC分期系统进一步完善预后的预测。2004年,Onken等[28]采用原发性UM转录组分析中的无监督聚类揭示了基于GEP的两个分类,预后较好的1类和预后较差的2类。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应用,补充了驱动基因层面的研究,鉴定了UM的初级驱动基因(GNAQ、GNA11)和次级驱动基因(BAP1、SF3B1、EIF1MX)。约90%的UM存在GNAQ、GNA11基因突变,激活肿瘤的发生。BAP1基因突变临床预后最差,SF3B1次之,EIF1MX最佳[29]。
Pandiani等[12]对6个原发性UM肿瘤行scRNA-seq分析,针对1 000个最多变基因行主成分分析,将细胞和基因按照主成分(PC)分数排序,构建了基于PC值的预后预测模型。采用TCGA数据库进行Kaplan-Meier验证,PC值高的基因与总体存活率低相关。其中,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成分β2-微球蛋白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A都是PC值高的基因,而在UM中HLA Ⅰ类或HLA Ⅱ类抗原的高表达预示预后差[30]。
Strub等[13]评价了4种预后模型对生存率的预测能力,包括单体3、基于基因表达和DNA 甲基化谱提取出的11个预后相关基因签名[31]、GEP分型[28]、单细胞分析构建的PC1模型。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每种预后分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它们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79、077、0.85、0.85,证实了基于PC值的签名预测预后更加准确。
Liu等[32]使用GSE139839数据集(Durante的单细胞测序数据)探索与UM免疫环境相关的m6A调节因子和长链非编码RNA,开发基于m6A的基因签名有助于提高对患者的预后预测。
CD8+ T细胞被认为是UM不良预后的指标[33]。Sun等[34]探索了CD8+ T细胞在UM中预测预后和对免疫治疗反应的作用。通过结合GSE139839数据集(Durante的单细胞测序数据),筛选出与CD8+ T细胞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采用多种机器学习的算法构建了CD8+ T细胞相关的基因签名,包括3个与肿瘤或免疫反应相关基因IFNGR1、ANXA6和TANK。这种基因签名可促进免疫监测,拯救耗尽的CD8+ T细胞,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疗效。
综上所述,在单细胞水平上,从RNA甲基化、免疫等不同角度挖掘预后的生物学特征,结合人工智能方法,可以辅助完善预后相关的分子指标体系。
2.4 scRNA-seq有助于寻找治疗靶点
Gαq信号通路的激活是UM进展中常见的早期事件,主要特点是GNAQ或GNA11基因突变,还包括较罕见的基因CYSLTR2[35]。基因CYSLTR2编码G蛋白偶联受体半胱氨酸白三烯受体2(CysLT2R),该受体参与白三烯介导的信号传导[36]。CYSLTR2基因突变导致内源性Gαq信号激活,从而刺激与GNAQ和GNA11中致癌突变相同的途径[37]。
Nell等[38]用数字型聚合酶链反应结合公共数据库分析发现,CYSLTR2基因参与UM的早期和晚期进展。其中,CYSLTR2p.L129Q突变可能是起始致癌事件。随着肿瘤进展,CYSLTR2突变等位基因的表达丰度不断增加,结果说明突变型CysLT2R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Pandiani等[12]发现转录因子HES6在UM中具有驱动肿瘤的侵袭性和不良预后等重要作用;该研究运用鸡胚绒毛尿囊膜试验证实,HES6的缺失会在体外和体内抑制肿瘤增生、迁移和转移播散。这提示,HES6及其靶基因可能作为治疗的靶点。
3 不足与展望
单细胞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样本要求高、测序花费昂贵和耗时长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完善和分析方法的更新,这些缺点可被逐步解决。目前公开的仅有17个UM样本的单细胞测序数据,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具有局限性,不适用于所有患者。此外,除了已经阐明的研究问题,还可对公开的单细胞数据挖掘,更加细致的研究肿瘤的起源、进展和免疫浸润。最终,将研究结果回归临床,开发出有效的诊断、预后分级和治疗肿瘤转移的方法,才能最大地发挥单细胞测序的优势。
UM是成人眼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因其易转移、对化学治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均不敏感的特点,使得转移的早期诊断、治疗和干预都十分困难。肿瘤的异质性增加了探索UM生物学特征的复杂性。对UM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挑战,许多问题至今还在探索中,例如如何识别肿瘤转移早期,如何有效治疗肿瘤转移且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等。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发展为研究者和患者带来了希望,随着技术的更新和不断完善,未来终将攻克这一罕见肿瘤,实现UM患者长期生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