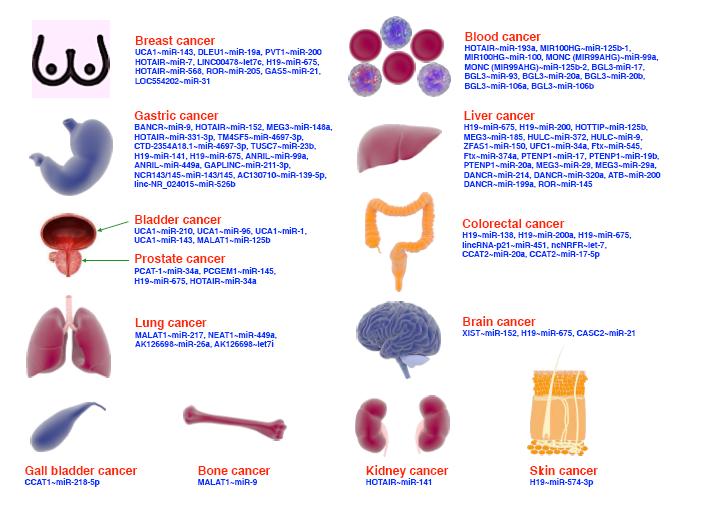引用本文: 麻婧, 李松峰, 刘敬花, 邓光达, 李亮, 原铭贞, 周丹, 卢海. 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治疗合并玻璃体积血的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疗效分析.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3, 39(1): 34-40.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20512-00296 复制
版权信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期刊社《中华眼底病杂志》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改编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XLRS)是一种相对罕见的遗传性视网膜变性类疾病,以黄斑和周边视网膜层间劈裂为典型临床表现,玻璃体积血(VH)和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可导致患者视力明显下降[1-3]。既往认为XLRS的VH是由于劈裂层间血管撕裂造成,无需特殊治疗,密切随访观察即可[1]。但随着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技术的应用,临床发现XLRS可合并视网膜、视盘、脉络膜新生血管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新生血管继发VH,以及血管渗漏和无灌注区[4-7]。有研究认为,视网膜劈裂可以造成内层视网膜缺血缺氧,从而导致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增高,新生血管形成[7-9]。抗VEGF药物治疗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和Coats病等儿童血管性眼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证实[10],目前关于抗VEGF药物治疗XLRS 合并VH的研究尚少。Hu等[11]报道4例合并VH或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的XLRS患者应用雷珠单抗或贝伐单抗治疗后积血迅速吸收、无严重并发症发生,但随访时间较短,且部分病例同时合并其他眼部疾病。我们对一组XLRS合并VH患者行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治疗,观察治疗后VH吸收时间、视力变化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号:TREC2022-KY060);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原则,患者监护人均获知情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2016年3月1日至2022年4月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XLRS并发VH患者18例19只眼纳入本研究。纳入标准:(1)符合XLRS临床诊断标准[1];(2)男性;(3)患眼或对侧眼眼底检查和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显示存在黄斑劈裂,伴或不伴周边视网膜劈裂;(4)具有阳性家族史;(5)行基因检测者发现异常RS1基因;(6)患眼存在VH。排除伴其他眼部疾病、外伤或全身疾病者。VH分级标准:0级,无VH,黄斑区细节可见;1级,仅黄斑区细节不可见,三级视网膜小动脉可见;2级,仅一、二级视网膜动脉可见;3级,仅视盘可见;4级,仅红光反射可见。IVR治疗适应证:VH浓厚且遮盖后极部视网膜影响视力;或反复VH,次数≥2次。
患眼均行验光、裂隙灯显微镜、间接检眼镜、广角眼底彩色照相、OCT检查以及眼轴长度(AL)测量。行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6只眼。行基因检测6例。BCVA检查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进行,统计时换算为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广角眼底彩色照相采用英国Optos公司Optomap 2000广角视网膜照相机和(或)美国Clarity公司第三代广域数字化小儿视网膜成像系统(RetCam Ⅲ)进行。采用德国Heidelberg公司Spectralis HRA+OCT仪和(或)美国Optvue公司 RTVue XR OCT仪测量患眼黄斑中心凹厚度(CMT)。CMT为黄斑中心凹1 mm范围视网膜内界膜内表面至视网膜色素上皮(RPE)层外表面的平均垂直距离。
患者均为男性;年龄(7.05±3.85)(3~16)岁。BCVA光感~0.16。行基因检测的6例,异常RS1基因均为错义突变。依据是否接受IVR治疗,将患者分为注药组、观察组,分别为10例11只眼、8例8只眼。注药组11只眼中,VH浓厚且遮盖后极部视网膜9只眼,其中伴明显牵拉拟行玻璃体切割手术(PPV),手术前预防性给予抗VEGF药物治疗1只眼;VH次数≥2次者2只眼。均于全身麻醉下行玻璃体腔注射10 mg/ml的雷珠单抗0.025 ml(含雷珠单抗0.25 mg)治疗。观察组患者均为监护人拒绝接受IVR治疗或等待手术过程中VH部分吸收。两组患者年龄、BCVA、屈光度、AL、VH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2)。
 )
)
治疗后1周及1、3、6、12个月定期随访。因患者治疗后恢复情况和居住地不同,具体随访时间间隔有所差异。注药组患者治疗后随访时间(24.82±20.77)(1~72)个月。随访时采用治疗前相同的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注药组11只眼中,单纯IVR治疗前后有眼底照相对比资料9只眼;后期行PPV 2只眼,无单纯IVR治疗前后眼底照相对比资料。观察组8只眼中,随访期间有眼底照相资料7只眼;后期行PPV 1只眼,无单纯观察眼底照相资料。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VH前后、IVR治疗前后BCVA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吸收时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是否进行IVR治疗、VH分级、VH后BCVA对VH吸收时间的影响。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分级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VH前后、IVR治疗前后BCVA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吸收时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是否进行IVR治疗、VH分级、VH后BCVA对VH吸收时间的影响。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分级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VH前后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0.73±0.32、1.80±0.77;VH后BCVA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20,P=0.006)。
所有患眼黄斑区均有不同程度劈裂,且合并周边视网膜劈裂(均未累及黄斑)。其中,劈裂区存在内层孔16只眼(84.2%,16/19);存在血管改变(图1A,1B)13只眼(72.2%,13/19),包括“桥样”血管、血管白鞘、血管扭曲、“霜样树枝样”改变等。行FFA检查的6只眼,均可见明显毛细血管渗漏,其中大片明显无灌注区4只眼,团状强荧光2只眼(图1C)。注药组患眼中有IVR治疗前后眼底照相资料的9只眼,治疗后异常血管消退1只眼(图1D),随访2年未再出现;周边劈裂范围均无明显改变(图2A~2C)。FFA检查显示,治疗后9只眼劈裂区域内广泛毛细血管扩张渗漏(图2D)。
 图1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1A示彩色眼底像,劈裂区域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B示彩色眼底像,颞下血管弓旁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C示图1A同眼FFA像,异常血管相应位置荧光素团状渗漏(白色线框内),劈裂区域内广泛无灌注区及毛细血管明显渗漏;1D示图1B同眼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后2年彩色眼底像,异常血管消退(白色线框内)
图1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1A示彩色眼底像,劈裂区域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B示彩色眼底像,颞下血管弓旁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C示图1A同眼FFA像,异常血管相应位置荧光素团状渗漏(白色线框内),劈裂区域内广泛无灌注区及毛细血管明显渗漏;1D示图1B同眼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后2年彩色眼底像,异常血管消退(白色线框内)
 图2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玻璃体积血(VH)前后、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治疗前后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2A~2C分别示VH前、VH后、IVR治疗后15个月彩色眼底像,可见陈旧和新鲜VH并存,IVR治疗后周边劈裂无改变;2D示图2A同眼IVR治疗后FFA像,下方大片无灌注区,劈裂区域内广泛毛细血管扩张渗漏
图2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玻璃体积血(VH)前后、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治疗前后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2A~2C分别示VH前、VH后、IVR治疗后15个月彩色眼底像,可见陈旧和新鲜VH并存,IVR治疗后周边劈裂无改变;2D示图2A同眼IVR治疗后FFA像,下方大片无灌注区,劈裂区域内广泛毛细血管扩张渗漏
行OCT检查的2只眼中,1只眼IVR治疗前后CMT分别为519、651 μm;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CMT增加25.4%。1只眼IVR 治疗前后CMT分别为203、201 μm,劈裂腔位于神经节细胞层及内核层;治疗后劈裂腔及CMT未见明显改变。
注药组患眼VH后、IVR治疗后logMAR BCVA分别为1.87±0.55、0.62±0.29;IVR治疗后BCVA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684,P<0.001)。IVR治疗前后均有BCVA记录5只眼,治疗后BCVA提高、无变化分别为1、4只眼。VH后、IVR治疗后logMAR BCVA分别为0.58±0.31、0.48±0.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00,P=0.374)。观察组8只眼中,VH前、VH吸收后均有BCVA记录5只眼。VH吸收后,BCVA无变化4只眼;降低1只眼,为反复发生VH者。VH前、VH吸收后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0.88±0.28、0.90±0.2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00,P=0.374)。末次随访时,注药组、观察组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0.59±0.17、0.94±0.25。
注药组、观察组患眼VH吸收时间分别为(1.80±1.06)、(7.25±5.04)个月;注药组患眼VH吸收时间较观察组显著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05,P=0.018)。纳入VH分级、VH后BCVA及是否IVR治疗构建多因素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是否IVR治疗与VH吸收时间显著相关(P<0.05)。VH分级、VH后BCVA与VH吸收时间无相关性(P>0.05)(表3)。
注药组患眼中,IVR治疗后发生再积血者1只眼,出血量较少、吸收迅速、未影响视力。IVR治疗前反复积血3次者1只眼,治疗后随访1年以上未观察到再积血。手术前预防性给予IVR治疗的1只眼,治疗后1周行PPV。因VH浓厚,IVR治疗后未完全吸收且伴增生牵拉行PPV 1只眼;手术后随访17个月未观察到再积血,视力维持稳定。观察组8只眼中,发生再积血2只眼。其中,反复再积血3次者1只眼;因观察1年积血未吸收完全1只眼,行PPV治疗。RetCam行眼底检查后出现轻微点状角膜上皮损伤1只眼,给予抗生素滴眼液治疗后恢复。注药组、观察组患眼再积血眼数、行PPV眼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76、1.000)。
注药组患眼中,少量结膜下出血2只眼;轻微角膜上皮点状损伤1只眼。均在短期内自行恢复。所有患者未出现感染性眼内炎、黄斑裂孔、视网膜脱离、并发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等严重并发症,且无全身相关并发症。
3 讨论
XLRS是一种伴X连锁隐性遗传眼病,多在学龄前因发现视力差就诊,初期视力一般比较稳定或缓慢下降,如果发生VH或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则会突然视力下降。文献报道约4%~40%的患者会出现VH,且多见于儿童或青少年期[2,12]。儿童期为视力发育的关键时期,少量VH可以自行吸收不影响视力,但反复VH、积血吸收不完全导致的屈光间质混浊可以严重影响视力发育[13-14]。本研究结果显示,与观察组比较,注药组患眼因IVR治疗加快了积血吸收进程,缩短了患儿因屈光间质混浊而影响视觉发育的时间,患儿视力预后更好。
根据文献报道,XLRS患者VH的可能原因除传统认为的血管受牵拉破裂之外,还有可能与新生血管形成有关[2,7,15]。长期视网膜劈裂造成的视网膜慢性缺血、缺氧可能会导致VEGF含量上调和血管通透性改变[7-8],导致内皮细胞增生、细胞迁移、血管渗漏、缺氧部位的血管新生[16]。多篇文献报道过XLRS劈裂区域内外的异常新生血管形成以及继发VH的病例[4-7];另有文献报道老年性视网膜劈裂和高度近视视网膜劈裂患者中也有类似新生血管相关病例[8-9]。本研究中,注药组1只眼VH前眼底可见异常血管,IVR治疗后消退且未再出现;1只眼FFA可见团状强荧光素渗漏的异常血管,位于劈裂区域边缘,其旁有广泛毛细血管渗漏及大片无灌注区域,与文献报道类似[15,17]。本研究中部分患眼存在陈旧和新鲜积血并存的情况,可能与位于劈裂边缘附近的异常血管反复受牵拉出血有关,抗VEGF药物治疗可能通过抑制和稳定异常血管,减少再积血,从而使VH更快吸收。有研究报道,抗VEGF药物治疗可以加速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VH的吸收,可能与抑制新生血管、减少再积血和血管渗漏有关[18-20]。Hu等[11]报道,玻璃体腔多次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XLRS合并VH(3只眼)、渗出性视网膜脱离(1只眼)(4例雷珠单抗,其中1例联合贝伐单抗),VH吸收迅速,未发现严重并发症。
相较于成年人,儿童玻璃体视网膜手术难度更大、并发症更多、手术后更难配合体位要求[21]。XLRS患者手术指征包括浓厚、反复VH、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及部分牵拉性视网膜脱离[22]。本研究中注药组患眼均为VH浓厚或反复VH者, 1只眼曾出现多次VH,IVR治疗后随访1年以上未观察到再积血;1只眼IVR治疗后出现再积血,且第2次积血迅速吸收,未影响视力。观察组患眼中再积血比例更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1只眼观察过程中反复VH4次,FFA检查显示异常团状强荧光素渗漏及大片无灌注区,考虑反复VH可能与异常血管受牵拉有关,但由于监护人拒绝接受抗VEGF药物或手术治疗,目前仍处于观察过程中。注药组患眼中仅1只眼因IVR治疗后积血未完全吸收且合并明确牵拉而接受PPV;观察组患眼中1只眼1年后积血仍未吸收且伴有机化而行PPV。注药组患眼再积血比例更小,因VH再次接受PPV的比例更小,可能与抗VEGF药物治疗抑制和稳定异常血管有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与总体病例数较少、观察组中VH分级较低的病例数较多等因素有关,需要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来探究抗VEGF药物治疗是否能让更多患者免除PPV相关风险。
安全性方面,有研究报道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可能会导致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患眼玻璃体增生、机化,进而导致牵拉性视网膜脱离[23]。机械性牵拉是XLRS患者劈裂发生与发展的因素之一[2]。本研究经长期随访观察,未见周边视网膜劈裂进展或玻璃体机化增生导致牵拉视网膜脱离的发生和发展。行OCT检查的2只眼中,1只眼黄斑区劈裂未见明显改变,BCVA无改变;1只眼IVR治疗后CMT较之前增加25.4%,但BCVA无改变。有文献报道,由于XLRS患者CMT在自然病程中本身即存在波动,显著增厚的标准应为增加22.4%~28.0%以上[24-25]。目前尚无有关XLRS患者抗VEGF药物治疗后劈裂及增生改变的研究。但有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合并脉络膜新生血管患者接受康柏西普治疗后,黄斑区劈裂变化与抗VEGF药物治疗次数无关[26]。抗VEGF药物治疗与XLRS患者黄斑区和周边视网膜劈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前瞻性、大样本研究明确。本研究中仅2只眼出现少量结膜下出血且自行吸收,注药组和观察组中各1只眼点状角膜上皮损伤,可能和RetCam眼底照相的接触性检查有关。注药组所有患眼均未发生感染性眼内炎、视网膜脱离、继发性青光眼、并发性白内障、黄斑裂孔等眼部严重并发症。雷珠单抗因不含Fc片段,无法与内皮细胞Fc受体结合,在血浆内更容易被清除,半衰期更短[27]。有前瞻性研究表明,IVR治疗后系统性VEGF含量几乎不受影响,本研究随访过程中亦未见患者出现全身系统相关并发症[28]。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为小样本量、回顾性研究,尚需扩大病例数、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并对比抗VEGF药物治疗前后FFA表现,以及黄斑区OCT结构改变。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XLRS)是一种相对罕见的遗传性视网膜变性类疾病,以黄斑和周边视网膜层间劈裂为典型临床表现,玻璃体积血(VH)和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可导致患者视力明显下降[1-3]。既往认为XLRS的VH是由于劈裂层间血管撕裂造成,无需特殊治疗,密切随访观察即可[1]。但随着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技术的应用,临床发现XLRS可合并视网膜、视盘、脉络膜新生血管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新生血管继发VH,以及血管渗漏和无灌注区[4-7]。有研究认为,视网膜劈裂可以造成内层视网膜缺血缺氧,从而导致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增高,新生血管形成[7-9]。抗VEGF药物治疗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和Coats病等儿童血管性眼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证实[10],目前关于抗VEGF药物治疗XLRS 合并VH的研究尚少。Hu等[11]报道4例合并VH或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的XLRS患者应用雷珠单抗或贝伐单抗治疗后积血迅速吸收、无严重并发症发生,但随访时间较短,且部分病例同时合并其他眼部疾病。我们对一组XLRS合并VH患者行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治疗,观察治疗后VH吸收时间、视力变化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号:TREC2022-KY060);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原则,患者监护人均获知情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2016年3月1日至2022年4月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XLRS并发VH患者18例19只眼纳入本研究。纳入标准:(1)符合XLRS临床诊断标准[1];(2)男性;(3)患眼或对侧眼眼底检查和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显示存在黄斑劈裂,伴或不伴周边视网膜劈裂;(4)具有阳性家族史;(5)行基因检测者发现异常RS1基因;(6)患眼存在VH。排除伴其他眼部疾病、外伤或全身疾病者。VH分级标准:0级,无VH,黄斑区细节可见;1级,仅黄斑区细节不可见,三级视网膜小动脉可见;2级,仅一、二级视网膜动脉可见;3级,仅视盘可见;4级,仅红光反射可见。IVR治疗适应证:VH浓厚且遮盖后极部视网膜影响视力;或反复VH,次数≥2次。
患眼均行验光、裂隙灯显微镜、间接检眼镜、广角眼底彩色照相、OCT检查以及眼轴长度(AL)测量。行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6只眼。行基因检测6例。BCVA检查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进行,统计时换算为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广角眼底彩色照相采用英国Optos公司Optomap 2000广角视网膜照相机和(或)美国Clarity公司第三代广域数字化小儿视网膜成像系统(RetCam Ⅲ)进行。采用德国Heidelberg公司Spectralis HRA+OCT仪和(或)美国Optvue公司 RTVue XR OCT仪测量患眼黄斑中心凹厚度(CMT)。CMT为黄斑中心凹1 mm范围视网膜内界膜内表面至视网膜色素上皮(RPE)层外表面的平均垂直距离。
患者均为男性;年龄(7.05±3.85)(3~16)岁。BCVA光感~0.16。行基因检测的6例,异常RS1基因均为错义突变。依据是否接受IVR治疗,将患者分为注药组、观察组,分别为10例11只眼、8例8只眼。注药组11只眼中,VH浓厚且遮盖后极部视网膜9只眼,其中伴明显牵拉拟行玻璃体切割手术(PPV),手术前预防性给予抗VEGF药物治疗1只眼;VH次数≥2次者2只眼。均于全身麻醉下行玻璃体腔注射10 mg/ml的雷珠单抗0.025 ml(含雷珠单抗0.25 mg)治疗。观察组患者均为监护人拒绝接受IVR治疗或等待手术过程中VH部分吸收。两组患者年龄、BCVA、屈光度、AL、VH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2)。
 )
)
治疗后1周及1、3、6、12个月定期随访。因患者治疗后恢复情况和居住地不同,具体随访时间间隔有所差异。注药组患者治疗后随访时间(24.82±20.77)(1~72)个月。随访时采用治疗前相同的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注药组11只眼中,单纯IVR治疗前后有眼底照相对比资料9只眼;后期行PPV 2只眼,无单纯IVR治疗前后眼底照相对比资料。观察组8只眼中,随访期间有眼底照相资料7只眼;后期行PPV 1只眼,无单纯观察眼底照相资料。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VH前后、IVR治疗前后BCVA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吸收时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是否进行IVR治疗、VH分级、VH后BCVA对VH吸收时间的影响。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分级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VH前后、IVR治疗前后BCVA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吸收时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是否进行IVR治疗、VH分级、VH后BCVA对VH吸收时间的影响。注药组与观察组之间VH分级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VH前后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0.73±0.32、1.80±0.77;VH后BCVA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20,P=0.006)。
所有患眼黄斑区均有不同程度劈裂,且合并周边视网膜劈裂(均未累及黄斑)。其中,劈裂区存在内层孔16只眼(84.2%,16/19);存在血管改变(图1A,1B)13只眼(72.2%,13/19),包括“桥样”血管、血管白鞘、血管扭曲、“霜样树枝样”改变等。行FFA检查的6只眼,均可见明显毛细血管渗漏,其中大片明显无灌注区4只眼,团状强荧光2只眼(图1C)。注药组患眼中有IVR治疗前后眼底照相资料的9只眼,治疗后异常血管消退1只眼(图1D),随访2年未再出现;周边劈裂范围均无明显改变(图2A~2C)。FFA检查显示,治疗后9只眼劈裂区域内广泛毛细血管扩张渗漏(图2D)。
 图1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1A示彩色眼底像,劈裂区域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B示彩色眼底像,颞下血管弓旁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C示图1A同眼FFA像,异常血管相应位置荧光素团状渗漏(白色线框内),劈裂区域内广泛无灌注区及毛细血管明显渗漏;1D示图1B同眼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后2年彩色眼底像,异常血管消退(白色线框内)
图1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1A示彩色眼底像,劈裂区域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B示彩色眼底像,颞下血管弓旁异常血管(白色线框内);1C示图1A同眼FFA像,异常血管相应位置荧光素团状渗漏(白色线框内),劈裂区域内广泛无灌注区及毛细血管明显渗漏;1D示图1B同眼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后2年彩色眼底像,异常血管消退(白色线框内)
 图2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玻璃体积血(VH)前后、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治疗前后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2A~2C分别示VH前、VH后、IVR治疗后15个月彩色眼底像,可见陈旧和新鲜VH并存,IVR治疗后周边劈裂无改变;2D示图2A同眼IVR治疗后FFA像,下方大片无灌注区,劈裂区域内广泛毛细血管扩张渗漏
图2
X连锁视网膜劈裂症患眼玻璃体积血(VH)前后、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治疗前后彩色眼底、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像。2A~2C分别示VH前、VH后、IVR治疗后15个月彩色眼底像,可见陈旧和新鲜VH并存,IVR治疗后周边劈裂无改变;2D示图2A同眼IVR治疗后FFA像,下方大片无灌注区,劈裂区域内广泛毛细血管扩张渗漏
行OCT检查的2只眼中,1只眼IVR治疗前后CMT分别为519、651 μm;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CMT增加25.4%。1只眼IVR 治疗前后CMT分别为203、201 μm,劈裂腔位于神经节细胞层及内核层;治疗后劈裂腔及CMT未见明显改变。
注药组患眼VH后、IVR治疗后logMAR BCVA分别为1.87±0.55、0.62±0.29;IVR治疗后BCVA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684,P<0.001)。IVR治疗前后均有BCVA记录5只眼,治疗后BCVA提高、无变化分别为1、4只眼。VH后、IVR治疗后logMAR BCVA分别为0.58±0.31、0.48±0.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00,P=0.374)。观察组8只眼中,VH前、VH吸收后均有BCVA记录5只眼。VH吸收后,BCVA无变化4只眼;降低1只眼,为反复发生VH者。VH前、VH吸收后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0.88±0.28、0.90±0.2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00,P=0.374)。末次随访时,注药组、观察组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0.59±0.17、0.94±0.25。
注药组、观察组患眼VH吸收时间分别为(1.80±1.06)、(7.25±5.04)个月;注药组患眼VH吸收时间较观察组显著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05,P=0.018)。纳入VH分级、VH后BCVA及是否IVR治疗构建多因素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是否IVR治疗与VH吸收时间显著相关(P<0.05)。VH分级、VH后BCVA与VH吸收时间无相关性(P>0.05)(表3)。
注药组患眼中,IVR治疗后发生再积血者1只眼,出血量较少、吸收迅速、未影响视力。IVR治疗前反复积血3次者1只眼,治疗后随访1年以上未观察到再积血。手术前预防性给予IVR治疗的1只眼,治疗后1周行PPV。因VH浓厚,IVR治疗后未完全吸收且伴增生牵拉行PPV 1只眼;手术后随访17个月未观察到再积血,视力维持稳定。观察组8只眼中,发生再积血2只眼。其中,反复再积血3次者1只眼;因观察1年积血未吸收完全1只眼,行PPV治疗。RetCam行眼底检查后出现轻微点状角膜上皮损伤1只眼,给予抗生素滴眼液治疗后恢复。注药组、观察组患眼再积血眼数、行PPV眼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76、1.000)。
注药组患眼中,少量结膜下出血2只眼;轻微角膜上皮点状损伤1只眼。均在短期内自行恢复。所有患者未出现感染性眼内炎、黄斑裂孔、视网膜脱离、并发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等严重并发症,且无全身相关并发症。
3 讨论
XLRS是一种伴X连锁隐性遗传眼病,多在学龄前因发现视力差就诊,初期视力一般比较稳定或缓慢下降,如果发生VH或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则会突然视力下降。文献报道约4%~40%的患者会出现VH,且多见于儿童或青少年期[2,12]。儿童期为视力发育的关键时期,少量VH可以自行吸收不影响视力,但反复VH、积血吸收不完全导致的屈光间质混浊可以严重影响视力发育[13-14]。本研究结果显示,与观察组比较,注药组患眼因IVR治疗加快了积血吸收进程,缩短了患儿因屈光间质混浊而影响视觉发育的时间,患儿视力预后更好。
根据文献报道,XLRS患者VH的可能原因除传统认为的血管受牵拉破裂之外,还有可能与新生血管形成有关[2,7,15]。长期视网膜劈裂造成的视网膜慢性缺血、缺氧可能会导致VEGF含量上调和血管通透性改变[7-8],导致内皮细胞增生、细胞迁移、血管渗漏、缺氧部位的血管新生[16]。多篇文献报道过XLRS劈裂区域内外的异常新生血管形成以及继发VH的病例[4-7];另有文献报道老年性视网膜劈裂和高度近视视网膜劈裂患者中也有类似新生血管相关病例[8-9]。本研究中,注药组1只眼VH前眼底可见异常血管,IVR治疗后消退且未再出现;1只眼FFA可见团状强荧光素渗漏的异常血管,位于劈裂区域边缘,其旁有广泛毛细血管渗漏及大片无灌注区域,与文献报道类似[15,17]。本研究中部分患眼存在陈旧和新鲜积血并存的情况,可能与位于劈裂边缘附近的异常血管反复受牵拉出血有关,抗VEGF药物治疗可能通过抑制和稳定异常血管,减少再积血,从而使VH更快吸收。有研究报道,抗VEGF药物治疗可以加速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VH的吸收,可能与抑制新生血管、减少再积血和血管渗漏有关[18-20]。Hu等[11]报道,玻璃体腔多次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XLRS合并VH(3只眼)、渗出性视网膜脱离(1只眼)(4例雷珠单抗,其中1例联合贝伐单抗),VH吸收迅速,未发现严重并发症。
相较于成年人,儿童玻璃体视网膜手术难度更大、并发症更多、手术后更难配合体位要求[21]。XLRS患者手术指征包括浓厚、反复VH、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及部分牵拉性视网膜脱离[22]。本研究中注药组患眼均为VH浓厚或反复VH者, 1只眼曾出现多次VH,IVR治疗后随访1年以上未观察到再积血;1只眼IVR治疗后出现再积血,且第2次积血迅速吸收,未影响视力。观察组患眼中再积血比例更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1只眼观察过程中反复VH4次,FFA检查显示异常团状强荧光素渗漏及大片无灌注区,考虑反复VH可能与异常血管受牵拉有关,但由于监护人拒绝接受抗VEGF药物或手术治疗,目前仍处于观察过程中。注药组患眼中仅1只眼因IVR治疗后积血未完全吸收且合并明确牵拉而接受PPV;观察组患眼中1只眼1年后积血仍未吸收且伴有机化而行PPV。注药组患眼再积血比例更小,因VH再次接受PPV的比例更小,可能与抗VEGF药物治疗抑制和稳定异常血管有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与总体病例数较少、观察组中VH分级较低的病例数较多等因素有关,需要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来探究抗VEGF药物治疗是否能让更多患者免除PPV相关风险。
安全性方面,有研究报道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可能会导致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患眼玻璃体增生、机化,进而导致牵拉性视网膜脱离[23]。机械性牵拉是XLRS患者劈裂发生与发展的因素之一[2]。本研究经长期随访观察,未见周边视网膜劈裂进展或玻璃体机化增生导致牵拉视网膜脱离的发生和发展。行OCT检查的2只眼中,1只眼黄斑区劈裂未见明显改变,BCVA无改变;1只眼IVR治疗后CMT较之前增加25.4%,但BCVA无改变。有文献报道,由于XLRS患者CMT在自然病程中本身即存在波动,显著增厚的标准应为增加22.4%~28.0%以上[24-25]。目前尚无有关XLRS患者抗VEGF药物治疗后劈裂及增生改变的研究。但有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合并脉络膜新生血管患者接受康柏西普治疗后,黄斑区劈裂变化与抗VEGF药物治疗次数无关[26]。抗VEGF药物治疗与XLRS患者黄斑区和周边视网膜劈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前瞻性、大样本研究明确。本研究中仅2只眼出现少量结膜下出血且自行吸收,注药组和观察组中各1只眼点状角膜上皮损伤,可能和RetCam眼底照相的接触性检查有关。注药组所有患眼均未发生感染性眼内炎、视网膜脱离、继发性青光眼、并发性白内障、黄斑裂孔等眼部严重并发症。雷珠单抗因不含Fc片段,无法与内皮细胞Fc受体结合,在血浆内更容易被清除,半衰期更短[27]。有前瞻性研究表明,IVR治疗后系统性VEGF含量几乎不受影响,本研究随访过程中亦未见患者出现全身系统相关并发症[28]。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为小样本量、回顾性研究,尚需扩大病例数、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并对比抗VEGF药物治疗前后FFA表现,以及黄斑区OCT结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