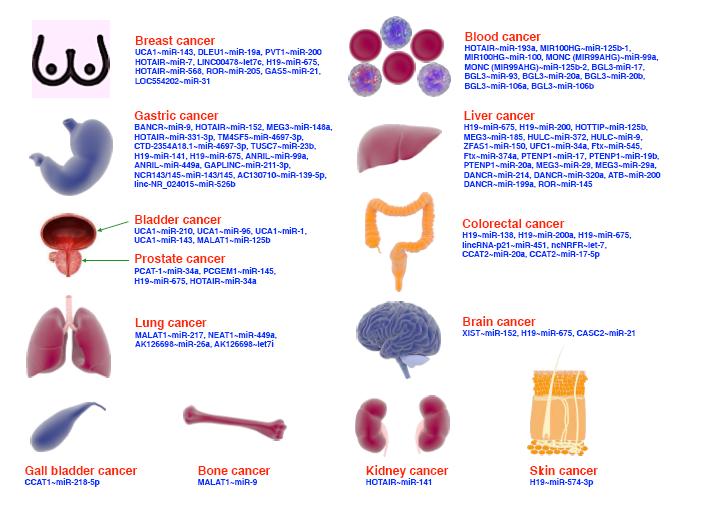自1998年以来,BEST1基因突变已被报道可导致Best卵黄状黄斑营养不良症(BVMD)等至少五种不同的临床表型,统称为“Best病”。现有研究已发现超过300种BEST1基因不同位点的突变,可能会引起其编码的钙激活阴离子通道蛋白1(BEST1)蛋白质错误转运、蛋白质寡聚缺陷以及阴离子通道活性异常等蛋白功能障碍,从而导致不同的疾病表现。然而Best病多样的临床表型和BEST1基因不同突变位点的对应关系仍不明确,针对Best病的药物和基因治疗仍在基础研究阶段,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临床选择基因治疗方案时,需要将患者临床表型和分子诊断结合起来考虑,明确界定其突变类型及致病机制,才能达到更好的个性化治疗效果。
版权信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期刊社《中华眼底病杂志》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改编
BEST1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1q13上,其编码的钙激活阴离子通道蛋白1(BEST1)已被证明主要表达于人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细胞,是一种定位在基底侧质膜上的膜蛋白,其既是一种阴离子通道,也能对细胞内钙信号转导进行调节[1-4]。1998年,BEST1基因突变首次被报道与Best卵黄状黄斑营养不良症(BVMD)相关[5-6]。近年来已报道的BEST1基因突变致病位点超过300个,可导致多种具有显著临床特征差异性的视网膜病变表型,统称为“Best病”,包括BVMD、常染色体隐性遗传Best病(ARB)、成年型卵黄状黄斑营养不良症(AVMD)、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病(ADVIRC)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RP)等[7-10]。目前,Best病仍是一组缺乏有效治疗的疾病。BEST1基因突变可能会导致BEST1蛋白错误转运及定位、通道蛋白寡聚异常及离子通道功能异常等缺陷而致病。不同的BEST1基因突变导致临床上不同的疾病表型的具体机制至今仍不明确。现就Best病与BEST1基因突变致病机制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今后对Best病致病机制和治疗靶点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1 BEST1基因
1.1 BEST1基因的表达与定位
既往研究通过Northern印迹分析首次发现BEST1基因在人类视网膜中的表达量最高,其次是大脑和脊髓[5-6]。2000年,首次报道BEST1基因编码的BEST1蛋白主要在人RPE中表达,而在视网膜神经上皮层、睫状体、虹膜、角膜或晶状体等其他眼部组织中均未发现BEST1蛋白表达[3]。除RPE外,也有研究在小鼠和人类呼吸道、结肠、肾脏、中枢神经系统的部分区域、结肠癌细胞和人类胰腺导管细胞系中也观察到BEST1蛋白的表达[7-12]。
1.2 BEST1蛋白通道的结构特征
BEST1蛋白由58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具有四个跨膜结构域(TMD),通过形成同源五聚体构成一个有中心孔的、旋转对称的花瓶状跨膜离子通道[13-14]。BEST1蛋白离子通道总长度约为95 Å,其胞外段入口直径约为20 Å、具有电负性,可排斥大多数阴离子(尤其是二价阴离子)[15]。该通道轴向有“颈部”和“孔口”两个主要狭窄限制点,其中“颈部”区域直径仅约6 Å、由TMD2上的三个高度保守的指向通道中轴的疏水残基I76、F80和F84组成,这些疏水氨基酸在调控通道功能和阴离子通过的选择性中起着关键作用[15-22]。在“颈部”的狭窄之后,通道形成一个长45 Å、宽20 Å的内腔,其构成了通道细胞内段的主体,并带有大量正电荷以吸引细胞内的阴离子[15-16]。在接近末端时,由于V205(在鸡类来源BEST1蛋白中)或I205(在人类BEST1蛋白中)的限制,通道再次变狭窄,形成“孔口”[19, 23]。
研究表明,“颈部”和“孔口”两种结构都参与Ca2+对于通道的门控作用[17, 24-26]。BEST1蛋白离子通道的同源五聚体分布有对称的Ca2+结合位点,称为“Ca2+扣环”,其位于通道的胞内部分,靠近颈部区域。Ca2+扣环和颈部是通道Ca2+依赖性门控装置的主要组成部分。Ca2+的结合与否调节着五聚体“颈部”缩窄区域在两种构象状态之间动态转变:未结合Ca2+时为封闭状态,直径为3.5 Å,其中I76、F80和F84残基产生疏水屏障,阻止离子渗透;结合Ca2+时为开放状态,直径为13 Å,其中F80和F84残基远离“颈部”中心,允许水合离子渗透,但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15, 23, 27]。
2 BEST1蛋白在RPE细胞中的功能
2.2 Ca2+激活的阴离子通道
BEST1蛋白已被证明是一种Ca2+激活的Cl-通道,对RPE中的Cl-转运至关重要[3, 24, 28]。2015年,Marmorstein等[2]使用人胎儿RPE(fhRPE)单层细胞发现,表达BVMD蛋白突变体Best1W93C的fhRPE单层细胞的跨上皮电位明显降低,而过表达野生型(WT)BEST1蛋白的跨上皮电位升高。而用葡萄糖酸盐代替水浴培养基中的Cl-会降低过表达WT BEST1的单层细胞的跨上皮电位,但对表达Best1W93C的单层细胞没有影响,这证明BEST1蛋白可通过影响RPE细胞内阴离子电流来提高其跨上皮电位[2]。Milenkovic等[3]通过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证实来自健康对照组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RPE中BEST1蛋白具有体积调节性阴离子通道的特征和功能特性[3]。基于鸡BEST1蛋白的研究结果表明,“孔口”结构主要决定了通道的阴离子通透性,阴离子必须至少部分脱水才能通过狭窄“孔口”结构,通道对单价阴离子通透性与离子脱水能力的倒数相对应,通透性从高到低顺序为:SCN->NO3->I->Br->Cl->F-[15, 16, 20-21, 27, 29-34]。
此外,定位在细胞膜上的BEST1蛋白会对细胞内浓度低至纳摩尔范围的Ca2+有所反应,使阴离子沿着其电化学梯度流经通道穿过细胞膜。这种细胞内游离Ca2+的主要来源是通过代谢信号通路缓慢释放的内部储存的Ca2+以及质膜上Ca2+通道激活[26]。Kane Dickson等[16]将在乙二醇双α-氨基乙基醚四乙酸中重组的BEST1蛋白脂质体稀释到含有Cl-和不同浓度游离Ca2+的溶液中,荧光检测法可观察到荧光的减少取决于Ca2+的浓度,且仅在含有BEST1蛋白晶体的脂质体中才能观察到Cl-通量,表明Ca2+激活了Cl-向脂质体的渗透,也初步证实了BEST1蛋白是一种Ca2+激活的Cl-通道。随后,Vaisey等[15]通过电生理手段揭示“颈部”和“Ca2+扣环”结构主要组成了一个Ca2+依赖门控装置,进一步证明了BEST1蛋白作为Ca2+依赖Cl-通道的机制:Ca2+扣环作为细胞内Ca2+的传感器,而颈部作为一个有效的“门”,当通道未结合Ca2+时,“颈部”限制Cl-和其他阴离子的流动,并在Ca2+结合时允许它们通过。
2.3 调控RPE细胞内Ca2+水平
除了作为阴离子通道发挥作用外,BEST1蛋白还被证实具有细胞内Ca2+信号传导和Ca2+平衡的调节器作用[35]。2006年,Rosenthal等[36]首次报道了BEST1蛋白对RPE-J细胞中L型电压依赖性Ca2+通道的动力学有显著影响。Yu等[37]使用人胚胎肾细胞293(HEK293)细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BEST1蛋白还可以由胞内C端结构域介导与L型电压依赖性Ca2+通道的β3和β4亚基发生物理和功能上的相互作用[36-39]。研究表明,BEST1蛋白与β4亚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它向细胞质膜的转运[42-43]。在RPE模型中的研究表明,BEST1蛋白通过传导Cl-离子,来帮助细胞积累和释放Ca2+离子[40-42]。然而,仍需更多研究证明BEST1蛋白对Ca2+的影响到底是其阴离子通道活性的下游作用,还是一种单独的功能。在对原代RPE(fhRPE、iPSC-RPE)模型的研究中也提示,BEST1蛋白会影响细胞内的钙信号转导,致病突变会破坏钙稳态[2, 4]。钙稳态的独特变化可能是Best病的病理基础,并可能用于区分各类Best病。
2.4 阴离子通道作用受三磷酸腺苷(ATP)调控
目前已有研究证明,除了Ca2+之外,与ATP的结合也能增加BEST1蛋白的离子通道活性。Zhang等[43]用纯化的肺炎克雷伯氏菌Best蛋白同源物(KpBest)发现,ATP会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显著增加BEST1蛋白通道的开放率,并用全细胞膜片钳检测iPSC-RPE中不同ATP浓度条件下的Ca2+依赖性Cl-电流,发现峰值电流随着ATP浓度升高显著增强,由此确定了ATP是BEST1蛋白的辅助激活剂,能使通道活性增加约3倍。
BEST1蛋白通道作用受ATP调控也在结构研究上得到了支持。研究者通过对KpBest、人BEST1蛋白和牛BEST2蛋白进行比对,确定了BEST1蛋白细胞内环上的四个候选ATP结合基团(环1~环4),进而证实在KpBest中,环2特别参与了ATP结合和通道的ATP依赖性激活[43]。在P274R基因突变iPSC-RPE中的全细胞膜片钳测量结果提示,环1~环3与ATP结合相关而环4并不参与ATP依赖性激活。这些结果也与所报道的突变发生在环1~环3的临床现象相一致[43]。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根据高度保守的KpBest和鸡BEST1蛋白结构构建了一个三维人类同源模型,其中的ATP结合基团(残基199-203)位于与通道激活门(I205)相邻的环2上,进一步明确了BEST1蛋白的ATP结合位点,并表明其可能是通道门控的关键位点[43]。综上,研究者提出了一种BEST1蛋白通道的两步激活模型:在没有Ca2+和ATP的情况下,通道处于关闭状态;单独与Ca2+结合的通道处于部分开放状态;与Ca2+和ATP结合的通道处于完全开放状态,阐释了Ca2+与ATP对于BEST1蛋白通道的协同调控作用[47]。
3 BEST1基因突变与Best病
3.1 不同Best病的遗传模式差异
目前报道的Best病的临床表型包括BVMD、ARB、AVMD、ADVIRC以及RP等。每种亚型的分子病因与遗传方式均有所不同,临床特征也有差异。
BVMD是Best病中最常见的一种,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其基因表达十分多样,其中大多为杂合错义突变。在临床上,BEST1基因突变导致的AVMD与PRPH2基因突变导致的AVMD是否有区别尚不明确。由于AVMD和BVMD患者的临床表现非常相似,甚至无法区分,因此有研究者建议,携带BEST1基因突变并被诊断为AVMD的患者应被重新归类BVMD[23]。ARB是Best病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青少年黄斑营养不良症[48]。ARB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为BEST1基因的双位点突变,典型为纯合子突变,但临床以复合杂合子突变更常见[7]。ADVIRC是一种较为罕见的Best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1982年,Yang等[49]首次报道该疾病。既往研究证明,ADVIRC是由于外显子跳跃而导致的蛋白缩短和功能异常的一种突变表型[44]。此外,BEST1基因突变也可导致RP。2009年,Lee等[10]首次报道了5个诊断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RP的家系以及相关的4个错义突变。一些报告表明,BEST1基因突变诱导的RP可能是一种多基因疾病,患者同时会具有其他RP相关基因[50]。
3.2 BEST1基因突变致病机制研究
截至2021年,共报道389个不同的BEST1基因位点突变[45]。包含303个错义突变、20个框内突变、63个截短突变、1个拷贝数异常、1个启动子缺失和1个3’UTR突变。其中,303个已发表的错义突变中,其中70.3%患者报道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Best病,包括BVMD、AVMD、ADVIRC和显性RP,而20.1%患者报道的错义突变为ARB[52-54]。研究表明,不同种族的变异热点突变亦有差异,包括中国患者的p.Glu300Lys、丹麦患者的p.Asp302Asn27和意大利患者的p.Arg25Trp(表1)。Best病具有显著的遗传异质性和临床异质性,不同突变位点的致病病理机制尚不明确,目前研究主要从突变位点的定位与功能出发,对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探索。
研究表明,与BVMD、AVMD、ARB和RP相关的BEST1蛋白突变体的阴离子电流会严重减弱,并且在与WT BEST1蛋白共表达时会抑制通道活性[2, 59-60]。Milenkovic等[3]发现,BVMD相关基因突变A243V或Q238R患者来源的iPSC-RPE中,体积调节的氯离子电流严重减少。Li等[24]发现,P274R和I201T突变患者来源的iPSC-RPE中表面Ca2+依赖性Cl-电流会完全消失或显著降低,进一步证实BEST1致病突变可能抑制RPE中Ca2+依赖的Cl-电流。研究还通过对应的KpBest P239R和L177T突变体模型证明,P274R突变是由于BEST1蛋白结构被破坏而导致的错误定位以及通道活性丧失;而I201T由于结构改变微小而不会改变BEST1蛋白的正确定位和对Ca2+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与I201T患者相比,P274R患者表现出更严重的视网膜表型,这表明BEST1蛋白的定位与功能、RPE表面Ca2+依赖性Cl-电流和视网膜正常生理之间都存在密切联系。
尽管已经报道的BEST1基因突变导致的蛋白结构或功能异常类型不同,但最终致病原因大都是因为RPE基底侧质膜上正常的BEST1蛋白离子通道功能异常。然而,不同Best病临床表型相关的突变与其干扰BEST1蛋白作为阴离子通道功能的对应关系仍不明确,不同的BEST1突变是否会影响RPE细胞中除氯离子以外的其他阴离子的转运也仍待进一步研究。
3.2.1 蛋白寡聚异常抑制其阴离子通道功能
鉴于BEST1蛋白的特殊晶体结构,部分BEST1基因突变可能通过破坏寡聚化并阻碍离子通道的正常形成而致病[16-17]。研究报道,与ADVIRC、AVMD、ARB、RP和BVMD相关的32个致病突变体,每一个突变体都能与WT BEST1蛋白发生物理相互作用,提示杂合患者中突变体无法与WT BEST1蛋白聚合并不是独立致病因素[57-58]。Sun等[30]研究发现,即使是严重截短的突变体如174Qfs*57和R200X也能与WT BEST1蛋白相互作用,提示BEST1蛋白结构的前174个氨基酸足以介导其寡聚化[61]。通过对一位ARB患者R141H和I366fsx18复合杂合突变的研究,两个位点突变的表达产物均能与iPSC-RPE细胞中的内源性BEST1蛋白相互作用,但R141H突变BEST1蛋白与正常BEST1蛋白的共聚不会引起疾病表型,而与I366fsX18突变BEST1蛋白的共聚会导致ARB[62]。由于两种组合都会产生可观的Cl−电流,表明该患者的ARB不是由通道失活引起的,考虑到I366fsX18突变BEST1蛋白仅由正常BEST1蛋白的前366个氨基酸组成,缺失大部分胞质内C末端结构域,提示后端的丢失可能是引起该患者ARB表型的病理机制[62]。
3.2.2 蛋白错误定位导致阴离子通道结构障碍
大量研究表明,BEST1蛋白定位于RPE的基底侧质膜,而BEST1基因部分特定位点突变可能通过引起BEST1蛋白向质膜的转运障碍,进而因质膜上缺少具有正常功能的BEST1蛋白而抑制了其阴离子通道活性而致病。从而导致疾病发生[1, 68-69]。此外,尽管大多数错误定位的突变体都在细胞内区室中,但不同的点突变会导致不同的定位模式,如R200X突变BEST1蛋白在整个细胞质中弥漫,而T6P突变BEST1蛋白更呈点状并集中在细胞核和顶端质膜之间,且错位定位在细胞质内的突变体蛋白会被蛋白酶体迅速降解[61, 66]。
此外,BEST1基因的不同突变对BEST1蛋白定位造成的影响还会随WT BEST1蛋白的存在与否而变化。在极化犬肾细胞(MDCK)细胞中的研究表明,当与WT BEST1蛋白共表达时,某些突变体会被部分“挽救”从而回到正确的细胞膜定位上。如WT BEST1蛋白和W93C突变BEST1蛋白共表达时,两种蛋白都会定位在基底侧质膜;而当与V9M突变BEST1蛋白共表达却会导致两种蛋白的错误定位[65]。由于MDCK细胞不表达内源性BEST1蛋白,同种突变体蛋白在RPE细胞和MDCK细胞中的定位也有差异。研究表明,错误定位的ARB相关M325T突变BEST1蛋白会导致WT BEST1蛋白的错误定位,但不会在杂合子患者中导致疾病表型,而正确定位的ARB相关突变体蛋白(如L472PfsX10)的纯合子患者仍然表现出ARB表型,表明突变蛋白的定位正确与否可能与ARB的疾病表型无关[61](表2)。
目前尚无研究明确不同突变BEST1蛋白与其转运定位情况和相关疾病间的对应关系。未来需有更多研究聚焦在不同人源RPE模型如iPSC-RPE、fhRPE或原代RPE中BEST1蛋白的转运定位情况,以探索在不同Best病临床表型中的蛋白错误定位的具体影响的差异及机制。
3.2.3 功能丧失突变与功能获得性突变的差异
绝大多数的患者来源突变表现出功能丧失表型,然而Ji等[25]发现了几种功能获得性突变(D203A、I205T和Y236C),当在HEK293细胞中瞬时表达时,这些突变会增强通道活性,但仍会引起Best病,这表明了维持正常BEST1基因生理功能的重要性。
通常来说,当BEST1常染色体显性突变仅存在于Best病患者的两个BEST1等位基因之一上时,即可识别出该突变。然而,这种方式只考虑了基因组基因的剂量,而忽略了等位基因的转录与表达水平。Zhao等[70]发现,6种常染色体显性的功能丧失突变体蛋白(A10T、R218H、L234P、A243T、Q293K和D302A)与WT BEST1以1∶1的比例表达与于HEK293细胞时,与仅表达WT BEST1蛋白所产生的电流相似;而当突变体WT BEST1蛋白以4∶1的比例共表达时,产生的Cl-电流才明显小于仅表达WT BEST1蛋白所产生的电流,与仅表达突变体所产生的电流相似。既往归类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部分Best病致病突变可能并非经典的显性遗传方式,而是当它们在体内的表达超过WT BEST1等位基因时表现出了显性负效应表型。此外,三种功能获得性突变(D203A、I205T和Y236C)均为经典的显性遗传方式。上述结论解释了携带相同BEST1突变的患者可能存在的不完全外显以及多样的临床表现,同时说明基因增补疗法可能只适用于功能丧失性突变,而对于功能获得性突变可能不能通过单独的基因增补来挽救,而需要与CRISPR-Cas9(成簇规律性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相关蛋白系统9)介导的内源性BEST1基因沉默相结合以恢复RPE细胞中Ca2+依赖的Cl-电流,提示了在选择基因治疗方案时鉴别突变类别的重要性[66]。
4 实验动物模型
BEST1相关黄斑病变的天然犬模型为犬多灶性视网膜病变(CMR)。引起这种犬视网膜疾病的犬BEST1基因突变有三种:过早终止突变(R25X)、错义突变(G161D)、以及框移突变(P463fs)。这些基因突变会在全球13个犬种中自发发生,都会导致同型受影响犬出现一致的临床表型,并模拟与人类疾病相似的临床、分子和组织学特征,包括黄斑中心凹部位(犬的黄斑区域)累及、发病和病程以及BEST1基因突变的分子后果[76-78]。以上原因使得犬Best病模型系统非常适合用于旨在了解Best病发病机制的研究。此外,由于BEST1基因突变相关黄斑病变在犬中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因此该模型也非常适合开发基因替代疗法等新型疗法[79](表3)。2004年,Marmorstein等[67]通过注射复制缺陷腺相关病毒(AAV),在大鼠RPE中过表达常见的BVMD相关突变体:W93C突变BEST1蛋白、R218C突变BEST1蛋白,在大鼠中建立了BVMD的暂态模型。视网膜电图(ERG)检查检测表明,突变体和WT BEST1蛋白均不会影响注射后活体大鼠的a波或b波。过表达WT BEST1蛋白增加了快速振荡和c波,而过表达突变体BEST1蛋白则降低了光峰的振幅。W93C突变BEST1蛋白明显改变了光峰反应函数,而R218C突变BEST1蛋白则没有影响。过表达WT BEST1蛋白会导致亮度反应函数的整体脱敏。数据还表明,在具有内源性WT BEST1蛋白蛋白的健康动物中,过表达突变体BEST1蛋白足以引起视网膜ERG异常[63]。
首个BEST1-/-基因敲除小鼠在Marmorstein等[74]的实验室产生,但已报道的基因敲除小鼠均未表现出与Best病类似的任何疾病表型或Cl-电流异常,只观察到了Ca2+电流的变化:当受到ATP刺激时,BEST1-/-小鼠的RPE与BEST1+/+幼鼠相比,Ca2+电流增加了五倍[74]。与BEST1基因敲除小鼠相比,基因敲入小鼠模型可表现出与BVMD相似的表型[75]。BEST1W93C/W93C和BEST1+/W93C小鼠会出现眼底可见的浆液性视网膜脱离以及脂褐质颗粒和未被吞噬的光感受器外节段的增加,ERG检查中的a波和b波正常,但光峰值亮度反应减弱。此外,这两种突变小鼠RPE在ATP刺激后未表现出Cl-电流异常,但却显示出Ca2+水平受抑制[71]。这与在BEST1-/-小鼠中观察到的反应相反。在这些小鼠模型中,BEST1蛋白对Ca2+水平影响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 Best病治疗的前沿研究方向
目前,尚无针对任何Best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不过,现有研究也已经展现出了一些有前景的临床方案。研究发现,单独使用丙戊酸或与雷帕霉素联合使用可提高BVMD iPSC-RPE中光感受器外节段的降解率[6, 76]。Uggenti等[80]研究发现,蛋白酶体抑制剂4-苯基丁酸酯处理四环素诱导表达ARB相关BEST1基因突变MDCKⅡ细胞,可恢复其氯离子传导功能,而4-苯基丁酸酯和第二种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的联合处理可将它们重新定位到基底侧质膜。此外,仍然还有大量其他候选药物有待探索[78]。
此外,由于眼球生理结构的特殊性,是非常适合开展基因治疗的人体器官。BEST1蛋白主要在人眼RPE中特异性表达,且仅由58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故针对其的基因治疗具有极佳的发展前景。此外,犬自然产生的CMR模型的临床表型与人类Best病相似,非常适合用作基因治疗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随着iPSC技术的发展,由患者iPSC分化而来的RPE细胞模型可以模拟Best病的许多特征,比如细胞通道活性降低、外节段吞噬功能障碍、脂褐素累积等[19, 28, 81, 82]。已有研究对功能丧失型BEST1基因突变患者来源的iPSC-RPE进行AAV介导的WT BEST1基因增补治疗,成功挽救其离子通道功能[82],而功能增益的BEST1基因突变也可通过基因扩增与CRISPR/Cas9介导的内源性BEST1基因表达敲除相结合的方法得到救治,为Best病的基因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66]。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对于一些较强的功能增益突变所致的Best病表型,单纯扩增WT BEST1似乎不足以挽救突变,因此该研究提出在基因扩增的同时可以进行基因沉默,抑制患者内源性BEST1基因,这种策略可能可以用于治疗所有类型的Best病[70]。Sinha等[83]使用非同源性末端接合方式对Best病进行基因编辑,成功恢复其离子通道功能,但脱靶效应的存在可能会影响细胞中其他基因的正常表达。综上所述,Best病的基因治疗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仍需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
6 小结与展望
目前,BEST1基因已报道超过300个不同的突变位点,可导致多种临床上不同形式的Best病表型。目前对BEST1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已有了初步认识,明确了BEST1蛋白是一种五聚体离子通道,在人类RPE中具有Ca2+依赖的阴离子通道功能以及调节细胞钙信号的作用。BEST1基因突变可能因造成BEST1蛋白的结构或定位异常而导致其阴离子通道功能受影响而致病。然而,各种突变造成的不同分子水平异常如何导致不同的临床表型仍然缺少更有说服力、更系统性的研究。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来阐释不同BEST1蛋白突变体的定位与功能、RPE表面Ca2+依赖性Cl-电流和视网膜正常生理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需要寻找更便捷、更能模拟人类Best病表型的动物模型以研究突变致病机制与治疗方案。此外,在临床选择基因治疗方案时,需要将患者临床表型和分子诊断结合起来考虑,明确界定其突变类型及致病机制,才能达到更好的个性化治疗效果。
BEST1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1q13上,其编码的钙激活阴离子通道蛋白1(BEST1)已被证明主要表达于人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细胞,是一种定位在基底侧质膜上的膜蛋白,其既是一种阴离子通道,也能对细胞内钙信号转导进行调节[1-4]。1998年,BEST1基因突变首次被报道与Best卵黄状黄斑营养不良症(BVMD)相关[5-6]。近年来已报道的BEST1基因突变致病位点超过300个,可导致多种具有显著临床特征差异性的视网膜病变表型,统称为“Best病”,包括BVMD、常染色体隐性遗传Best病(ARB)、成年型卵黄状黄斑营养不良症(AVMD)、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病(ADVIRC)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RP)等[7-10]。目前,Best病仍是一组缺乏有效治疗的疾病。BEST1基因突变可能会导致BEST1蛋白错误转运及定位、通道蛋白寡聚异常及离子通道功能异常等缺陷而致病。不同的BEST1基因突变导致临床上不同的疾病表型的具体机制至今仍不明确。现就Best病与BEST1基因突变致病机制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今后对Best病致病机制和治疗靶点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1 BEST1基因
1.1 BEST1基因的表达与定位
既往研究通过Northern印迹分析首次发现BEST1基因在人类视网膜中的表达量最高,其次是大脑和脊髓[5-6]。2000年,首次报道BEST1基因编码的BEST1蛋白主要在人RPE中表达,而在视网膜神经上皮层、睫状体、虹膜、角膜或晶状体等其他眼部组织中均未发现BEST1蛋白表达[3]。除RPE外,也有研究在小鼠和人类呼吸道、结肠、肾脏、中枢神经系统的部分区域、结肠癌细胞和人类胰腺导管细胞系中也观察到BEST1蛋白的表达[7-12]。
1.2 BEST1蛋白通道的结构特征
BEST1蛋白由58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具有四个跨膜结构域(TMD),通过形成同源五聚体构成一个有中心孔的、旋转对称的花瓶状跨膜离子通道[13-14]。BEST1蛋白离子通道总长度约为95 Å,其胞外段入口直径约为20 Å、具有电负性,可排斥大多数阴离子(尤其是二价阴离子)[15]。该通道轴向有“颈部”和“孔口”两个主要狭窄限制点,其中“颈部”区域直径仅约6 Å、由TMD2上的三个高度保守的指向通道中轴的疏水残基I76、F80和F84组成,这些疏水氨基酸在调控通道功能和阴离子通过的选择性中起着关键作用[15-22]。在“颈部”的狭窄之后,通道形成一个长45 Å、宽20 Å的内腔,其构成了通道细胞内段的主体,并带有大量正电荷以吸引细胞内的阴离子[15-16]。在接近末端时,由于V205(在鸡类来源BEST1蛋白中)或I205(在人类BEST1蛋白中)的限制,通道再次变狭窄,形成“孔口”[19, 23]。
研究表明,“颈部”和“孔口”两种结构都参与Ca2+对于通道的门控作用[17, 24-26]。BEST1蛋白离子通道的同源五聚体分布有对称的Ca2+结合位点,称为“Ca2+扣环”,其位于通道的胞内部分,靠近颈部区域。Ca2+扣环和颈部是通道Ca2+依赖性门控装置的主要组成部分。Ca2+的结合与否调节着五聚体“颈部”缩窄区域在两种构象状态之间动态转变:未结合Ca2+时为封闭状态,直径为3.5 Å,其中I76、F80和F84残基产生疏水屏障,阻止离子渗透;结合Ca2+时为开放状态,直径为13 Å,其中F80和F84残基远离“颈部”中心,允许水合离子渗透,但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15, 23, 27]。
2 BEST1蛋白在RPE细胞中的功能
2.2 Ca2+激活的阴离子通道
BEST1蛋白已被证明是一种Ca2+激活的Cl-通道,对RPE中的Cl-转运至关重要[3, 24, 28]。2015年,Marmorstein等[2]使用人胎儿RPE(fhRPE)单层细胞发现,表达BVMD蛋白突变体Best1W93C的fhRPE单层细胞的跨上皮电位明显降低,而过表达野生型(WT)BEST1蛋白的跨上皮电位升高。而用葡萄糖酸盐代替水浴培养基中的Cl-会降低过表达WT BEST1的单层细胞的跨上皮电位,但对表达Best1W93C的单层细胞没有影响,这证明BEST1蛋白可通过影响RPE细胞内阴离子电流来提高其跨上皮电位[2]。Milenkovic等[3]通过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证实来自健康对照组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RPE中BEST1蛋白具有体积调节性阴离子通道的特征和功能特性[3]。基于鸡BEST1蛋白的研究结果表明,“孔口”结构主要决定了通道的阴离子通透性,阴离子必须至少部分脱水才能通过狭窄“孔口”结构,通道对单价阴离子通透性与离子脱水能力的倒数相对应,通透性从高到低顺序为:SCN->NO3->I->Br->Cl->F-[15, 16, 20-21, 27, 29-34]。
此外,定位在细胞膜上的BEST1蛋白会对细胞内浓度低至纳摩尔范围的Ca2+有所反应,使阴离子沿着其电化学梯度流经通道穿过细胞膜。这种细胞内游离Ca2+的主要来源是通过代谢信号通路缓慢释放的内部储存的Ca2+以及质膜上Ca2+通道激活[26]。Kane Dickson等[16]将在乙二醇双α-氨基乙基醚四乙酸中重组的BEST1蛋白脂质体稀释到含有Cl-和不同浓度游离Ca2+的溶液中,荧光检测法可观察到荧光的减少取决于Ca2+的浓度,且仅在含有BEST1蛋白晶体的脂质体中才能观察到Cl-通量,表明Ca2+激活了Cl-向脂质体的渗透,也初步证实了BEST1蛋白是一种Ca2+激活的Cl-通道。随后,Vaisey等[15]通过电生理手段揭示“颈部”和“Ca2+扣环”结构主要组成了一个Ca2+依赖门控装置,进一步证明了BEST1蛋白作为Ca2+依赖Cl-通道的机制:Ca2+扣环作为细胞内Ca2+的传感器,而颈部作为一个有效的“门”,当通道未结合Ca2+时,“颈部”限制Cl-和其他阴离子的流动,并在Ca2+结合时允许它们通过。
2.3 调控RPE细胞内Ca2+水平
除了作为阴离子通道发挥作用外,BEST1蛋白还被证实具有细胞内Ca2+信号传导和Ca2+平衡的调节器作用[35]。2006年,Rosenthal等[36]首次报道了BEST1蛋白对RPE-J细胞中L型电压依赖性Ca2+通道的动力学有显著影响。Yu等[37]使用人胚胎肾细胞293(HEK293)细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BEST1蛋白还可以由胞内C端结构域介导与L型电压依赖性Ca2+通道的β3和β4亚基发生物理和功能上的相互作用[36-39]。研究表明,BEST1蛋白与β4亚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它向细胞质膜的转运[42-43]。在RPE模型中的研究表明,BEST1蛋白通过传导Cl-离子,来帮助细胞积累和释放Ca2+离子[40-42]。然而,仍需更多研究证明BEST1蛋白对Ca2+的影响到底是其阴离子通道活性的下游作用,还是一种单独的功能。在对原代RPE(fhRPE、iPSC-RPE)模型的研究中也提示,BEST1蛋白会影响细胞内的钙信号转导,致病突变会破坏钙稳态[2, 4]。钙稳态的独特变化可能是Best病的病理基础,并可能用于区分各类Best病。
2.4 阴离子通道作用受三磷酸腺苷(ATP)调控
目前已有研究证明,除了Ca2+之外,与ATP的结合也能增加BEST1蛋白的离子通道活性。Zhang等[43]用纯化的肺炎克雷伯氏菌Best蛋白同源物(KpBest)发现,ATP会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显著增加BEST1蛋白通道的开放率,并用全细胞膜片钳检测iPSC-RPE中不同ATP浓度条件下的Ca2+依赖性Cl-电流,发现峰值电流随着ATP浓度升高显著增强,由此确定了ATP是BEST1蛋白的辅助激活剂,能使通道活性增加约3倍。
BEST1蛋白通道作用受ATP调控也在结构研究上得到了支持。研究者通过对KpBest、人BEST1蛋白和牛BEST2蛋白进行比对,确定了BEST1蛋白细胞内环上的四个候选ATP结合基团(环1~环4),进而证实在KpBest中,环2特别参与了ATP结合和通道的ATP依赖性激活[43]。在P274R基因突变iPSC-RPE中的全细胞膜片钳测量结果提示,环1~环3与ATP结合相关而环4并不参与ATP依赖性激活。这些结果也与所报道的突变发生在环1~环3的临床现象相一致[43]。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根据高度保守的KpBest和鸡BEST1蛋白结构构建了一个三维人类同源模型,其中的ATP结合基团(残基199-203)位于与通道激活门(I205)相邻的环2上,进一步明确了BEST1蛋白的ATP结合位点,并表明其可能是通道门控的关键位点[43]。综上,研究者提出了一种BEST1蛋白通道的两步激活模型:在没有Ca2+和ATP的情况下,通道处于关闭状态;单独与Ca2+结合的通道处于部分开放状态;与Ca2+和ATP结合的通道处于完全开放状态,阐释了Ca2+与ATP对于BEST1蛋白通道的协同调控作用[47]。
3 BEST1基因突变与Best病
3.1 不同Best病的遗传模式差异
目前报道的Best病的临床表型包括BVMD、ARB、AVMD、ADVIRC以及RP等。每种亚型的分子病因与遗传方式均有所不同,临床特征也有差异。
BVMD是Best病中最常见的一种,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其基因表达十分多样,其中大多为杂合错义突变。在临床上,BEST1基因突变导致的AVMD与PRPH2基因突变导致的AVMD是否有区别尚不明确。由于AVMD和BVMD患者的临床表现非常相似,甚至无法区分,因此有研究者建议,携带BEST1基因突变并被诊断为AVMD的患者应被重新归类BVMD[23]。ARB是Best病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青少年黄斑营养不良症[48]。ARB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为BEST1基因的双位点突变,典型为纯合子突变,但临床以复合杂合子突变更常见[7]。ADVIRC是一种较为罕见的Best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1982年,Yang等[49]首次报道该疾病。既往研究证明,ADVIRC是由于外显子跳跃而导致的蛋白缩短和功能异常的一种突变表型[44]。此外,BEST1基因突变也可导致RP。2009年,Lee等[10]首次报道了5个诊断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RP的家系以及相关的4个错义突变。一些报告表明,BEST1基因突变诱导的RP可能是一种多基因疾病,患者同时会具有其他RP相关基因[50]。
3.2 BEST1基因突变致病机制研究
截至2021年,共报道389个不同的BEST1基因位点突变[45]。包含303个错义突变、20个框内突变、63个截短突变、1个拷贝数异常、1个启动子缺失和1个3’UTR突变。其中,303个已发表的错义突变中,其中70.3%患者报道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Best病,包括BVMD、AVMD、ADVIRC和显性RP,而20.1%患者报道的错义突变为ARB[52-54]。研究表明,不同种族的变异热点突变亦有差异,包括中国患者的p.Glu300Lys、丹麦患者的p.Asp302Asn27和意大利患者的p.Arg25Trp(表1)。Best病具有显著的遗传异质性和临床异质性,不同突变位点的致病病理机制尚不明确,目前研究主要从突变位点的定位与功能出发,对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探索。
研究表明,与BVMD、AVMD、ARB和RP相关的BEST1蛋白突变体的阴离子电流会严重减弱,并且在与WT BEST1蛋白共表达时会抑制通道活性[2, 59-60]。Milenkovic等[3]发现,BVMD相关基因突变A243V或Q238R患者来源的iPSC-RPE中,体积调节的氯离子电流严重减少。Li等[24]发现,P274R和I201T突变患者来源的iPSC-RPE中表面Ca2+依赖性Cl-电流会完全消失或显著降低,进一步证实BEST1致病突变可能抑制RPE中Ca2+依赖的Cl-电流。研究还通过对应的KpBest P239R和L177T突变体模型证明,P274R突变是由于BEST1蛋白结构被破坏而导致的错误定位以及通道活性丧失;而I201T由于结构改变微小而不会改变BEST1蛋白的正确定位和对Ca2+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与I201T患者相比,P274R患者表现出更严重的视网膜表型,这表明BEST1蛋白的定位与功能、RPE表面Ca2+依赖性Cl-电流和视网膜正常生理之间都存在密切联系。
尽管已经报道的BEST1基因突变导致的蛋白结构或功能异常类型不同,但最终致病原因大都是因为RPE基底侧质膜上正常的BEST1蛋白离子通道功能异常。然而,不同Best病临床表型相关的突变与其干扰BEST1蛋白作为阴离子通道功能的对应关系仍不明确,不同的BEST1突变是否会影响RPE细胞中除氯离子以外的其他阴离子的转运也仍待进一步研究。
3.2.1 蛋白寡聚异常抑制其阴离子通道功能
鉴于BEST1蛋白的特殊晶体结构,部分BEST1基因突变可能通过破坏寡聚化并阻碍离子通道的正常形成而致病[16-17]。研究报道,与ADVIRC、AVMD、ARB、RP和BVMD相关的32个致病突变体,每一个突变体都能与WT BEST1蛋白发生物理相互作用,提示杂合患者中突变体无法与WT BEST1蛋白聚合并不是独立致病因素[57-58]。Sun等[30]研究发现,即使是严重截短的突变体如174Qfs*57和R200X也能与WT BEST1蛋白相互作用,提示BEST1蛋白结构的前174个氨基酸足以介导其寡聚化[61]。通过对一位ARB患者R141H和I366fsx18复合杂合突变的研究,两个位点突变的表达产物均能与iPSC-RPE细胞中的内源性BEST1蛋白相互作用,但R141H突变BEST1蛋白与正常BEST1蛋白的共聚不会引起疾病表型,而与I366fsX18突变BEST1蛋白的共聚会导致ARB[62]。由于两种组合都会产生可观的Cl−电流,表明该患者的ARB不是由通道失活引起的,考虑到I366fsX18突变BEST1蛋白仅由正常BEST1蛋白的前366个氨基酸组成,缺失大部分胞质内C末端结构域,提示后端的丢失可能是引起该患者ARB表型的病理机制[62]。
3.2.2 蛋白错误定位导致阴离子通道结构障碍
大量研究表明,BEST1蛋白定位于RPE的基底侧质膜,而BEST1基因部分特定位点突变可能通过引起BEST1蛋白向质膜的转运障碍,进而因质膜上缺少具有正常功能的BEST1蛋白而抑制了其阴离子通道活性而致病。从而导致疾病发生[1, 68-69]。此外,尽管大多数错误定位的突变体都在细胞内区室中,但不同的点突变会导致不同的定位模式,如R200X突变BEST1蛋白在整个细胞质中弥漫,而T6P突变BEST1蛋白更呈点状并集中在细胞核和顶端质膜之间,且错位定位在细胞质内的突变体蛋白会被蛋白酶体迅速降解[61, 66]。
此外,BEST1基因的不同突变对BEST1蛋白定位造成的影响还会随WT BEST1蛋白的存在与否而变化。在极化犬肾细胞(MDCK)细胞中的研究表明,当与WT BEST1蛋白共表达时,某些突变体会被部分“挽救”从而回到正确的细胞膜定位上。如WT BEST1蛋白和W93C突变BEST1蛋白共表达时,两种蛋白都会定位在基底侧质膜;而当与V9M突变BEST1蛋白共表达却会导致两种蛋白的错误定位[65]。由于MDCK细胞不表达内源性BEST1蛋白,同种突变体蛋白在RPE细胞和MDCK细胞中的定位也有差异。研究表明,错误定位的ARB相关M325T突变BEST1蛋白会导致WT BEST1蛋白的错误定位,但不会在杂合子患者中导致疾病表型,而正确定位的ARB相关突变体蛋白(如L472PfsX10)的纯合子患者仍然表现出ARB表型,表明突变蛋白的定位正确与否可能与ARB的疾病表型无关[61](表2)。
目前尚无研究明确不同突变BEST1蛋白与其转运定位情况和相关疾病间的对应关系。未来需有更多研究聚焦在不同人源RPE模型如iPSC-RPE、fhRPE或原代RPE中BEST1蛋白的转运定位情况,以探索在不同Best病临床表型中的蛋白错误定位的具体影响的差异及机制。
3.2.3 功能丧失突变与功能获得性突变的差异
绝大多数的患者来源突变表现出功能丧失表型,然而Ji等[25]发现了几种功能获得性突变(D203A、I205T和Y236C),当在HEK293细胞中瞬时表达时,这些突变会增强通道活性,但仍会引起Best病,这表明了维持正常BEST1基因生理功能的重要性。
通常来说,当BEST1常染色体显性突变仅存在于Best病患者的两个BEST1等位基因之一上时,即可识别出该突变。然而,这种方式只考虑了基因组基因的剂量,而忽略了等位基因的转录与表达水平。Zhao等[70]发现,6种常染色体显性的功能丧失突变体蛋白(A10T、R218H、L234P、A243T、Q293K和D302A)与WT BEST1以1∶1的比例表达与于HEK293细胞时,与仅表达WT BEST1蛋白所产生的电流相似;而当突变体WT BEST1蛋白以4∶1的比例共表达时,产生的Cl-电流才明显小于仅表达WT BEST1蛋白所产生的电流,与仅表达突变体所产生的电流相似。既往归类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部分Best病致病突变可能并非经典的显性遗传方式,而是当它们在体内的表达超过WT BEST1等位基因时表现出了显性负效应表型。此外,三种功能获得性突变(D203A、I205T和Y236C)均为经典的显性遗传方式。上述结论解释了携带相同BEST1突变的患者可能存在的不完全外显以及多样的临床表现,同时说明基因增补疗法可能只适用于功能丧失性突变,而对于功能获得性突变可能不能通过单独的基因增补来挽救,而需要与CRISPR-Cas9(成簇规律性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相关蛋白系统9)介导的内源性BEST1基因沉默相结合以恢复RPE细胞中Ca2+依赖的Cl-电流,提示了在选择基因治疗方案时鉴别突变类别的重要性[66]。
4 实验动物模型
BEST1相关黄斑病变的天然犬模型为犬多灶性视网膜病变(CMR)。引起这种犬视网膜疾病的犬BEST1基因突变有三种:过早终止突变(R25X)、错义突变(G161D)、以及框移突变(P463fs)。这些基因突变会在全球13个犬种中自发发生,都会导致同型受影响犬出现一致的临床表型,并模拟与人类疾病相似的临床、分子和组织学特征,包括黄斑中心凹部位(犬的黄斑区域)累及、发病和病程以及BEST1基因突变的分子后果[76-78]。以上原因使得犬Best病模型系统非常适合用于旨在了解Best病发病机制的研究。此外,由于BEST1基因突变相关黄斑病变在犬中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因此该模型也非常适合开发基因替代疗法等新型疗法[79](表3)。2004年,Marmorstein等[67]通过注射复制缺陷腺相关病毒(AAV),在大鼠RPE中过表达常见的BVMD相关突变体:W93C突变BEST1蛋白、R218C突变BEST1蛋白,在大鼠中建立了BVMD的暂态模型。视网膜电图(ERG)检查检测表明,突变体和WT BEST1蛋白均不会影响注射后活体大鼠的a波或b波。过表达WT BEST1蛋白增加了快速振荡和c波,而过表达突变体BEST1蛋白则降低了光峰的振幅。W93C突变BEST1蛋白明显改变了光峰反应函数,而R218C突变BEST1蛋白则没有影响。过表达WT BEST1蛋白会导致亮度反应函数的整体脱敏。数据还表明,在具有内源性WT BEST1蛋白蛋白的健康动物中,过表达突变体BEST1蛋白足以引起视网膜ERG异常[63]。
首个BEST1-/-基因敲除小鼠在Marmorstein等[74]的实验室产生,但已报道的基因敲除小鼠均未表现出与Best病类似的任何疾病表型或Cl-电流异常,只观察到了Ca2+电流的变化:当受到ATP刺激时,BEST1-/-小鼠的RPE与BEST1+/+幼鼠相比,Ca2+电流增加了五倍[74]。与BEST1基因敲除小鼠相比,基因敲入小鼠模型可表现出与BVMD相似的表型[75]。BEST1W93C/W93C和BEST1+/W93C小鼠会出现眼底可见的浆液性视网膜脱离以及脂褐质颗粒和未被吞噬的光感受器外节段的增加,ERG检查中的a波和b波正常,但光峰值亮度反应减弱。此外,这两种突变小鼠RPE在ATP刺激后未表现出Cl-电流异常,但却显示出Ca2+水平受抑制[71]。这与在BEST1-/-小鼠中观察到的反应相反。在这些小鼠模型中,BEST1蛋白对Ca2+水平影响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 Best病治疗的前沿研究方向
目前,尚无针对任何Best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不过,现有研究也已经展现出了一些有前景的临床方案。研究发现,单独使用丙戊酸或与雷帕霉素联合使用可提高BVMD iPSC-RPE中光感受器外节段的降解率[6, 76]。Uggenti等[80]研究发现,蛋白酶体抑制剂4-苯基丁酸酯处理四环素诱导表达ARB相关BEST1基因突变MDCKⅡ细胞,可恢复其氯离子传导功能,而4-苯基丁酸酯和第二种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的联合处理可将它们重新定位到基底侧质膜。此外,仍然还有大量其他候选药物有待探索[78]。
此外,由于眼球生理结构的特殊性,是非常适合开展基因治疗的人体器官。BEST1蛋白主要在人眼RPE中特异性表达,且仅由58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故针对其的基因治疗具有极佳的发展前景。此外,犬自然产生的CMR模型的临床表型与人类Best病相似,非常适合用作基因治疗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随着iPSC技术的发展,由患者iPSC分化而来的RPE细胞模型可以模拟Best病的许多特征,比如细胞通道活性降低、外节段吞噬功能障碍、脂褐素累积等[19, 28, 81, 82]。已有研究对功能丧失型BEST1基因突变患者来源的iPSC-RPE进行AAV介导的WT BEST1基因增补治疗,成功挽救其离子通道功能[82],而功能增益的BEST1基因突变也可通过基因扩增与CRISPR/Cas9介导的内源性BEST1基因表达敲除相结合的方法得到救治,为Best病的基因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66]。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对于一些较强的功能增益突变所致的Best病表型,单纯扩增WT BEST1似乎不足以挽救突变,因此该研究提出在基因扩增的同时可以进行基因沉默,抑制患者内源性BEST1基因,这种策略可能可以用于治疗所有类型的Best病[70]。Sinha等[83]使用非同源性末端接合方式对Best病进行基因编辑,成功恢复其离子通道功能,但脱靶效应的存在可能会影响细胞中其他基因的正常表达。综上所述,Best病的基因治疗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仍需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
6 小结与展望
目前,BEST1基因已报道超过300个不同的突变位点,可导致多种临床上不同形式的Best病表型。目前对BEST1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已有了初步认识,明确了BEST1蛋白是一种五聚体离子通道,在人类RPE中具有Ca2+依赖的阴离子通道功能以及调节细胞钙信号的作用。BEST1基因突变可能因造成BEST1蛋白的结构或定位异常而导致其阴离子通道功能受影响而致病。然而,各种突变造成的不同分子水平异常如何导致不同的临床表型仍然缺少更有说服力、更系统性的研究。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来阐释不同BEST1蛋白突变体的定位与功能、RPE表面Ca2+依赖性Cl-电流和视网膜正常生理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需要寻找更便捷、更能模拟人类Best病表型的动物模型以研究突变致病机制与治疗方案。此外,在临床选择基因治疗方案时,需要将患者临床表型和分子诊断结合起来考虑,明确界定其突变类型及致病机制,才能达到更好的个性化治疗效果。